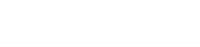第35章 苏晚晴 她也有一个幸福完满的家
火车在铿锵的车轮声中一路南下, 窗外的景色从北方的苍茫平原逐渐变为江南水乡的润泽葱茏。
两人抵达江城时,已是次日午后。湿润的空气夹杂着江水的气息扑面而来,与北方工业城市的干燥沉闷截然不同。
楚砚溪和陆哲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简陋的招待所安顿下来。
简单的休整后, 他们便按照事先的计划,开始分头行动。陆哲去寻找他年轻时的母亲沈静, 而楚砚溪的目标,则是她在这个世界年仅33岁的父亲楚同裕,以及……在江城师范大学任教的母亲苏晚晴, 还有那个刚刚几个月大的“自己”。
在楚砚溪的记忆里,母亲苏晚晴与父亲楚同裕结婚后,最开始住在母亲工作的江城师范大学分配的职工宿舍里,虽然是只有五十几平方米的小两房一厅,但一家三口住着还算宽敞。
楚砚溪的心跳有些快。
对于母亲苏晚晴, 她的感情复杂得像一团乱麻。在那个“真实”的世界里, 2005年,父亲楚同裕在一次抓捕持枪歹徒的行动中英勇牺牲,巨大的悲痛淹没了这个家,方才八岁的楚砚溪整日里哭泣着要找爸爸,母亲也悲痛万分。
然而,父亲去世后一年,母亲便接受了同校一位丧偶教授的追求, 组建了新的家庭,并很快有了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
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家里多了一个陌生男人、还有一个完全吸引了母亲所有注意力与关爱的妹妹——这一切, 对本就内心敏感不安的楚砚溪而言,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折磨。
楚砚溪害怕父亲被遗忘、害怕母亲被继父和妹妹夺走、更害怕自己的未来变得孤单、无依无靠,可是强烈的自尊心不允许她示弱,于是将所有的害怕化为愤怒。
她激烈反对母亲再婚, 抗拒继父的关心示好,讨厌妹妹的存在,整个人变得像刺猬一样,将所有尖刺竖起、拔出,并刺向亲人。
母亲苏晚晴不知道原本乖巧的女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放低姿态努力哄着楚砚溪,可是楚砚溪压根就不领情,她背着书包去了父亲最好的朋友秦峰家里,从此开启了住读生涯,就连寒暑假也不肯回母亲那个新家。
楚砚溪将母亲的再婚视为对父亲、对他们曾经幸福家庭的背叛,与母亲的关系降至冰点,沟通仅限于生活费转账和寥寥数语的电话短信。那份深埋心底的怨恨,像一根顽固的刺,多年来隐隐作痛。
楚砚溪已经忘记了父亲还在时母亲的模样,她真的很想知道,母亲是否刻骨铭心地爱过父亲?为什么那么轻易就将父亲遗忘?母亲是否也曾像对妹妹那样对待过她?为什么能够那么迅速地重新组建家庭?
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楚砚溪来到了江城市公安局附近。
下午三四点钟,春日略显无力的阳光斜照在门口悬挂的国徽上,反射出冷硬的光泽。楚砚溪没有靠近,而是站在马路对面绿荫处,耐心等待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楚砚溪的心情混杂着焦灼、期待和一丝近情情怯的惶恐。
终于,在临近下班时分,那个刻在骨子里的熟悉身影出现了。
33岁的楚同裕,穿着一身熨烫平整的警服,身姿挺拔如白杨,步伐矫健有力,眉宇间凝聚着刑警特有的锐利和专注,但嘴角似乎微微上扬,看来今天心情不错。
他熟练地跨上一辆半新的永久牌二八自行车,车把一拐,沿着栽满法国梧桐的林荫道,轻快地向师范大学所在的片区驶去。
楚砚溪立刻起身,快步跟上。
自行车铃叮当作响,穿过逐渐热闹起来的街市,楚同裕的车速不快,中间还停下来在路边摊买了点水果,他熟稔地和摊主打招呼,笑眯眯地挑选着苹果。
楚同裕的自行车最终驶入了一个环境清幽、挂着“江城师范大学教职工宿舍”牌子的小区。小区多是五六层高的红砖住宅楼,阳台外晾晒着衣物,花坛里种着些常见的花草,充满了安宁的生活气息。
楚砚溪看到父亲在五号楼前利落地停下自行车,落了锁,然后快步上了三楼。她站在楼下的香樟树投下的浓密阴影里,仰头望着那扇透着温暖灯光的窗户,心中百感交集。
那里,就是她在这个世界曾经拥有、却又彻底失去的“家”。
约莫半小时后,三楼的房门开了。先出来的是楚同裕,他一边下楼梯一边回头说着什么,脸上带着宠溺的笑容。紧接着,一个穿着浅灰色高领毛衣、外罩米色开衫、身形纤细苗条的年轻女子,抱着一个裹在鹅黄色绒毯里的婴儿,小心翼翼地走了下来。
那是28岁的母亲,苏晚晴。
春日傍晚的金色阳光如同温暖的蜜糖,流淌在她身上,勾勒出她温婉清丽的侧脸轮廓。她看起来非常年轻,皮肤白皙细腻,眉眼如画,带着江南女子特有的水秀和书卷气,但眉宇间依稀可见一丝疲惫——那是初为人母、昼夜操劳留下的痕迹。
苏晚晴低头凝视着怀中的婴儿时,眼神里充满了近乎虔诚的、浓得化不开的温柔爱意,嘴角噙着恬静而满足的浅笑。那种全身心投入的母性光辉,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柔和得不可思议。
楚同裕很自然地想接过她手中婴儿,苏晚晴却笑着轻轻摇头,稳稳地抱着孩子。楚同裕也不坚持,伸手极其轻柔地用指节蹭了蹭婴儿吹弹可破的小脸蛋,眼神里的爱意几乎要溢出来。
他低声嘱咐了几句,这才转身,大步流星地朝小区外走去。
苏晚晴则抱着孩子,走到楼前一张被阳光晒得暖洋洋的木制长椅旁坐下,轻轻摇晃着身体,哼着不成调的、软糯的江南摇篮曲,时不时低头用自己光洁的脸颊爱怜地蹭蹭婴儿的额头。
夕阳、母亲、婴儿,构成了一幅宁静美好的画卷。
楚砚溪站在斑驳的树影里,静静地、贪婪地看着这一幕。那颗因为童年创伤和多年积怨而冰封的心,因为这温暖的画面而有了融化的迹象。
原来,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自己的家曾经是这样的温暖。
原来,母亲也曾用这样毫无保留、专注到仿佛世界只剩下彼此的目光凝视过自己。
可为什么……为什么父亲牺牲后,那山盟海誓的感情、那曾经构筑起她整个世界的温暖堡垒,竟可以如此迅速地被另一个男人、另一个家庭所取代?
那份圣洁无比的母爱,难道也是可以如此轻易便转移的吗?
那股熟悉的、被最亲之人“背叛”的怨怼和尖锐的痛楚再次席卷而来,楚砚溪有些喘不上气来。
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从翻涌的情绪中抽离,整理了一下衣着和表情,从树影中走出,装作是小区新来的访客,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略带歉意的微笑,自然而然地走向那张沐浴在夕阳下的长椅。
楚砚溪在距离长椅几步远的地方停下,很礼貌地询问:“您好,请问这附近是不是有个邮局?”
苏晚晴闻声抬起头,看到是个面容清秀、气质沉静、眼神清澈的年轻姑娘,良好的教养让她态度很温和应:“邮局啊,出了小区大门往右拐,沿着师院路直走,大概过两个路口,在街角就能看到了,绿色的牌子,很显眼的。”
“谢谢您。”楚砚溪道了谢,目光却仿佛不经意地被吸引,落在她怀中那个咿呀作声、挥舞着小拳头的婴儿身上。
小家伙睁着乌溜溜、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正好奇地东张西望,小嘴咂巴着,粉嫩的脸颊肉嘟嘟的,可爱得让人心颤。
能够看到婴儿时期的自己,真是件很奇妙的事。
楚砚溪脸上的笑容根本就压不住:“您的宝宝真可爱,眼睛好大,多大了?”
提到孩子,苏晚晴嘴角带笑,声音里带着母亲特有的骄傲:“快六个月了。就是个小磨人精,晚上总睡不踏实,吵得人不得安生。”
“小孩子都这样的,长大点就好了,睡眠规律了就好了。”楚砚溪顺势在长椅的另一端坐下,保持着既不显疏远又不具侵略性的安全距离。
注意到苏晚晴眉宇间那抹的疲惫,楚砚溪的心抽疼了一下:“带宝宝一定很辛苦吧?孩子爸爸不帮忙吗?”
“还好,他爸爸工作忙,经常加班、出差,在家时间少。不过,只要一有空,他就会帮忙带孩子,换尿布、冲奶粉都抢着做。”苏晚晴的语气里带着对丈夫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甚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维护。
可是,楚砚溪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那隐藏在一瞥一笑间的落寞与担忧。警察的妻子,尤其是一线刑警的妻子,注定要承受比常人更多的孤独、牵挂和提心吊胆。
两人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从带孩子的各种琐碎不易,聊到江城湿润宜人的气候与北方的干燥对比,又隐约提及各自的情况。
楚砚溪称自己是来江城投奔亲戚、暂时借住在此的毕业生,正在寻找工作机会,言语间流露出对教师职业的尊敬,以及对苏晚晴既能照顾年幼孩子又能兼顾工作的钦佩和不易。
苏晚晴似乎也很久没遇到能如此平和聊天的年轻女性,渐渐放下了心防。楚砚溪看着她温柔拍哄孩子的侧影,听着她带着吴语软侬口音的普通话,心中那份芥蒂,在真实、鲜活、充满温情的接触下,开始松动、瓦解。
此时的苏晚晴,是一位深爱着女儿的母亲,一位关心着丈夫的妻子,一个努力在家庭和工作中寻找平衡的普通女性。她深爱着怀中的婴儿,承担着家中大部分家务,还要为刑警丈夫的安危担忧。
楚砚溪发现,自己长久以来固化的怨恨,在此刻面对如此真实的母亲时,竟有些无处着落。
想到父亲未来的命运,楚砚溪话锋一转,神色变得郑重而略带一丝神秘,她稍稍压低了声音,确保只有两人能听清:“冒昧问一句,您爱人从事的工作是否有一定的危险性?”
苏晚晴微微一怔,眼神里多了些明显的探究和警惕,身体也坐直了些。
楚砚溪迎着她的目光,语气诚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请您别见怪,我家里以前有位长辈,是乡间有名的相士,懂些相面望气之术,我自幼跟着学了点皮毛。方才我观您面相,子女宫饱满红润,是福泽深厚、晚运亨通之相,但是……”
她刻意停顿了一下,加重了语气,“您的夫妻宫,也就是眉尾上方、靠近鬓角的位置,此处隐约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青暗之气,主夫君未来恐会遭遇一场不小的劫难,此劫与金属利器相关,煞气颇重,可能会有血光之灾,危及性命。”
苏晚晴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抱着孩子的手下意识地收紧。婴儿感受到母亲骤然紧张的情绪,不安地扭动了一下,发出一阵哼哼声。苏晚晴一边哄着孩子,一边不安地打量着楚砚溪。
作为刑警的妻子,她对这些话有着远超常人的敏感和恐惧,丈夫职业的高风险性是她内心深处最不敢触碰的噩梦。
楚砚溪连忙放缓语气,带着安抚的意味:“您先别怕!凡事有因必有果,有劫亦可有解。破解之法不是没有。”
她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早准备好的锦囊递了过去。这个锦囊用暗红色绸布缝制、正面用金线绣着个古朴的“福”字,看着很精致。
“这个锦囊请您收好,里面是一个八卦铜镜,能帮您爱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请放在您爱人的左侧口袋里,贴身收藏。切记!七年之后的冬天,也就是2005年冬至那天不要外出,只要那天安全度过,此后便是坦途。”
楚砚溪有过两次穿越的经验,知道只要自己离开,所有关于她的记忆都会消失。不管她提醒父亲多少次,他总会忘记。因此这一次,她决定送点实物。
楚砚溪心中暗自思忖,父亲是个2005年冬至那天被刺中腰部左侧,脾脏破裂而死。这个铜镜一来能够替父亲挡刀,二来能在一定程度上让母亲记起自己说过的话,从而影响未来的轨迹,增加父亲生还的可能。
苏晚晴打开那个不过巴掌大小的秀气锦囊,看到里面有一面迷你小铜镜,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她抬眼看看楚砚溪异常认真的眼眸,内心有些复杂。
理智告诉她这陌生姑娘说的一切太过离奇,应该立刻拒绝。可是,眼前这个姑娘眼神干净,语气诚恳,不带丝毫市侩之气,尤其是那句“与金属利器相关,恐有血光之灾”,引发了她内心最深的恐惧。
她想起了丈夫每次深夜出紧急现场时自己彻夜不眠的煎熬,想起了他警服袖口偶尔蹭上的、洗不净的暗红痕迹,想起了他轻描淡写带过的那些惊险瞬间……
楚砚溪微笑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不是?我不找您要钱,也不要您任何东西,不过是因为和您聊得开心,又看宝宝可爱,所以才想着结个善缘。”
苏晚晴迟疑了一会,最终还是将这个锦囊紧紧攥在手心:“谢谢……”
楚砚溪暗暗松了口气,一直紧绷的心弦稍缓:“不客气。对我而言,这不过是举手之劳,但对您而言,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人生。”
她顿了顿,仿佛不经意地将目光重新投向那个可爱的婴儿,语气轻松地问,“宝宝长得真好,她叫什么名字?”
苏晚晴低头看着怀中的女儿,眼神重新被无尽的温柔爱意填满,声音也柔和下来:“叫砚溪。砚是笔墨纸砚的砚,溪是溪流的溪。希望她将来能文秀聪颖,像溪水一样,清澈、坚韧,汇溪成河,百川入海,拥有开阔的人生。”
真是一个承载了父母美好期望的名字。
楚砚溪伸出手,虚虚地、极轻极轻地抚了抚婴儿娇嫩得仿佛透明的小脸蛋,动作轻柔得像是怕惊扰了一场易碎的梦。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只有自己能听见,却蕴含着跨越了漫长时光洪流的、无尽复杂的情绪,有怜爱,有遗憾,有告诫,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悲伤:
“小砚溪,好好爱爸爸,爱妈妈,也要……好好爱自己。”
这句话,既是说给眼前这个尚在襁褓、对未来一无所知的婴儿,又何尝不是对那个在家庭剧变中受伤、多年来封闭内心、从未真正学会与母亲和解、与过去和解、更不懂得如何好好爱自己的、成年后的楚砚溪的深切告诫与期盼?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匆匆从小区门口走来,是买菜归来的楚同裕。他看到妻子正和陌生姑娘说话,立刻快步走了过来,警觉地将目光投向楚砚溪。
“晚晴,怎么了?没事吧?”他语气关切,脚步沉稳,不动声色地挡在了妻女身前,目光锐利地扫过楚砚溪,带着职业性的审视。虽然年轻,但刑警的本能让他对任何接近家人的陌生人都保持着警惕。
苏晚晴连忙将锦囊紧紧攥在手心,下意识地藏到身后:“没事,这位姑娘路过,问了个路,我们……随便聊了几句。”她并不想让丈夫知道刚才那番关于“血光之灾”的谈话,怕增加他的心理负担。
楚同裕看了看面前这个气质沉静、眼神清澈坦荡的陌生姑娘,眉头微蹙,但见对方确实不像歹人,妻女也无恙,便没有再多问,只是对楚砚溪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他随即转过身,极其自然地俯身,从苏晚晴臂弯里接过女儿,脸上绽放出毫无阴霾的、灿烂如孩童般的笑容,语气宠溺:“小溪,有没有想爸爸?嗯?”
那一刻,夕阳的最后一抹金辉正好笼罩在这温馨的三口之家身上。
楚同裕高大的身躯微微弯着,形成一个保护性的姿态,苏晚晴仰头看着他,眼中满是依赖与柔情,怀中的婴儿似乎被父亲逗弄,发出咿呀的、模糊的音节。幸福、安宁、充满爱意的气息几乎要满溢出来。
楚砚溪静静地站着,看着这一家三口。
眼前的幸福景象美好得如同油画,灼烧着她的眼睛和心脏。泪水毫无预兆地涌上眼眶,视线也变得模糊起来。楚砚溪迅速低下头,用力眨眼,逼退那些泪水。
曾经,她也有一个如此幸福完满的家,也曾被父亲这样稳稳抱起,被母亲这样温柔凝视。
可是,命运的齿轮却在冷酷地转动着,眼前这一切会消失、曾经的爱会转移、所有幸福都会荡然无存。只希望,她今天所做的一切,能够对抗那不公的命运,能够让眼前这一切美好永远延续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楚砚溪此刻内心酸楚无比。对命运无常的深切悲恸、对逝去幸福的锥心追忆,以及一种巨大的、无法融入的孤独感,种种强烈的情绪涌上心头,楚砚溪低声道了句再见,匆匆转身,快步走开。
走出很远,直到拐过街角,再也看不到那栋楼,楚砚溪才敢停下脚步,靠在冰凉的墙壁上,仰起头,深深呼吸着傍晚微凉的空气,试图平复汹涌的心潮。
夜幕开始降临,华灯初上。
江城师范大学教职工小区三楼那扇窗户里,温暖的灯光依旧亮着,隐约传来婴儿的啼哭和大人温柔的安抚声,那是人间最平凡的烟火气,也是楚砚溪此生无法再触及的遥远星河。
火车在铿锵的车轮声中一路南下, 窗外的景色从北方的苍茫平原逐渐变为江南水乡的润泽葱茏。
两人抵达江城时,已是次日午后。湿润的空气夹杂着江水的气息扑面而来,与北方工业城市的干燥沉闷截然不同。
楚砚溪和陆哲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简陋的招待所安顿下来。
简单的休整后, 他们便按照事先的计划,开始分头行动。陆哲去寻找他年轻时的母亲沈静, 而楚砚溪的目标,则是她在这个世界年仅33岁的父亲楚同裕,以及……在江城师范大学任教的母亲苏晚晴, 还有那个刚刚几个月大的“自己”。
在楚砚溪的记忆里,母亲苏晚晴与父亲楚同裕结婚后,最开始住在母亲工作的江城师范大学分配的职工宿舍里,虽然是只有五十几平方米的小两房一厅,但一家三口住着还算宽敞。
楚砚溪的心跳有些快。
对于母亲苏晚晴, 她的感情复杂得像一团乱麻。在那个“真实”的世界里, 2005年,父亲楚同裕在一次抓捕持枪歹徒的行动中英勇牺牲,巨大的悲痛淹没了这个家,方才八岁的楚砚溪整日里哭泣着要找爸爸,母亲也悲痛万分。
然而,父亲去世后一年,母亲便接受了同校一位丧偶教授的追求, 组建了新的家庭,并很快有了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
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家里多了一个陌生男人、还有一个完全吸引了母亲所有注意力与关爱的妹妹——这一切, 对本就内心敏感不安的楚砚溪而言,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折磨。
楚砚溪害怕父亲被遗忘、害怕母亲被继父和妹妹夺走、更害怕自己的未来变得孤单、无依无靠,可是强烈的自尊心不允许她示弱,于是将所有的害怕化为愤怒。
她激烈反对母亲再婚, 抗拒继父的关心示好,讨厌妹妹的存在,整个人变得像刺猬一样,将所有尖刺竖起、拔出,并刺向亲人。
母亲苏晚晴不知道原本乖巧的女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放低姿态努力哄着楚砚溪,可是楚砚溪压根就不领情,她背着书包去了父亲最好的朋友秦峰家里,从此开启了住读生涯,就连寒暑假也不肯回母亲那个新家。
楚砚溪将母亲的再婚视为对父亲、对他们曾经幸福家庭的背叛,与母亲的关系降至冰点,沟通仅限于生活费转账和寥寥数语的电话短信。那份深埋心底的怨恨,像一根顽固的刺,多年来隐隐作痛。
楚砚溪已经忘记了父亲还在时母亲的模样,她真的很想知道,母亲是否刻骨铭心地爱过父亲?为什么那么轻易就将父亲遗忘?母亲是否也曾像对妹妹那样对待过她?为什么能够那么迅速地重新组建家庭?
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楚砚溪来到了江城市公安局附近。
下午三四点钟,春日略显无力的阳光斜照在门口悬挂的国徽上,反射出冷硬的光泽。楚砚溪没有靠近,而是站在马路对面绿荫处,耐心等待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楚砚溪的心情混杂着焦灼、期待和一丝近情情怯的惶恐。
终于,在临近下班时分,那个刻在骨子里的熟悉身影出现了。
33岁的楚同裕,穿着一身熨烫平整的警服,身姿挺拔如白杨,步伐矫健有力,眉宇间凝聚着刑警特有的锐利和专注,但嘴角似乎微微上扬,看来今天心情不错。
他熟练地跨上一辆半新的永久牌二八自行车,车把一拐,沿着栽满法国梧桐的林荫道,轻快地向师范大学所在的片区驶去。
楚砚溪立刻起身,快步跟上。
自行车铃叮当作响,穿过逐渐热闹起来的街市,楚同裕的车速不快,中间还停下来在路边摊买了点水果,他熟稔地和摊主打招呼,笑眯眯地挑选着苹果。
楚同裕的自行车最终驶入了一个环境清幽、挂着“江城师范大学教职工宿舍”牌子的小区。小区多是五六层高的红砖住宅楼,阳台外晾晒着衣物,花坛里种着些常见的花草,充满了安宁的生活气息。
楚砚溪看到父亲在五号楼前利落地停下自行车,落了锁,然后快步上了三楼。她站在楼下的香樟树投下的浓密阴影里,仰头望着那扇透着温暖灯光的窗户,心中百感交集。
那里,就是她在这个世界曾经拥有、却又彻底失去的“家”。
约莫半小时后,三楼的房门开了。先出来的是楚同裕,他一边下楼梯一边回头说着什么,脸上带着宠溺的笑容。紧接着,一个穿着浅灰色高领毛衣、外罩米色开衫、身形纤细苗条的年轻女子,抱着一个裹在鹅黄色绒毯里的婴儿,小心翼翼地走了下来。
那是28岁的母亲,苏晚晴。
春日傍晚的金色阳光如同温暖的蜜糖,流淌在她身上,勾勒出她温婉清丽的侧脸轮廓。她看起来非常年轻,皮肤白皙细腻,眉眼如画,带着江南女子特有的水秀和书卷气,但眉宇间依稀可见一丝疲惫——那是初为人母、昼夜操劳留下的痕迹。
苏晚晴低头凝视着怀中的婴儿时,眼神里充满了近乎虔诚的、浓得化不开的温柔爱意,嘴角噙着恬静而满足的浅笑。那种全身心投入的母性光辉,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柔和得不可思议。
楚同裕很自然地想接过她手中婴儿,苏晚晴却笑着轻轻摇头,稳稳地抱着孩子。楚同裕也不坚持,伸手极其轻柔地用指节蹭了蹭婴儿吹弹可破的小脸蛋,眼神里的爱意几乎要溢出来。
他低声嘱咐了几句,这才转身,大步流星地朝小区外走去。
苏晚晴则抱着孩子,走到楼前一张被阳光晒得暖洋洋的木制长椅旁坐下,轻轻摇晃着身体,哼着不成调的、软糯的江南摇篮曲,时不时低头用自己光洁的脸颊爱怜地蹭蹭婴儿的额头。
夕阳、母亲、婴儿,构成了一幅宁静美好的画卷。
楚砚溪站在斑驳的树影里,静静地、贪婪地看着这一幕。那颗因为童年创伤和多年积怨而冰封的心,因为这温暖的画面而有了融化的迹象。
原来,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自己的家曾经是这样的温暖。
原来,母亲也曾用这样毫无保留、专注到仿佛世界只剩下彼此的目光凝视过自己。
可为什么……为什么父亲牺牲后,那山盟海誓的感情、那曾经构筑起她整个世界的温暖堡垒,竟可以如此迅速地被另一个男人、另一个家庭所取代?
那份圣洁无比的母爱,难道也是可以如此轻易便转移的吗?
那股熟悉的、被最亲之人“背叛”的怨怼和尖锐的痛楚再次席卷而来,楚砚溪有些喘不上气来。
她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从翻涌的情绪中抽离,整理了一下衣着和表情,从树影中走出,装作是小区新来的访客,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略带歉意的微笑,自然而然地走向那张沐浴在夕阳下的长椅。
楚砚溪在距离长椅几步远的地方停下,很礼貌地询问:“您好,请问这附近是不是有个邮局?”
苏晚晴闻声抬起头,看到是个面容清秀、气质沉静、眼神清澈的年轻姑娘,良好的教养让她态度很温和应:“邮局啊,出了小区大门往右拐,沿着师院路直走,大概过两个路口,在街角就能看到了,绿色的牌子,很显眼的。”
“谢谢您。”楚砚溪道了谢,目光却仿佛不经意地被吸引,落在她怀中那个咿呀作声、挥舞着小拳头的婴儿身上。
小家伙睁着乌溜溜、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正好奇地东张西望,小嘴咂巴着,粉嫩的脸颊肉嘟嘟的,可爱得让人心颤。
能够看到婴儿时期的自己,真是件很奇妙的事。
楚砚溪脸上的笑容根本就压不住:“您的宝宝真可爱,眼睛好大,多大了?”
提到孩子,苏晚晴嘴角带笑,声音里带着母亲特有的骄傲:“快六个月了。就是个小磨人精,晚上总睡不踏实,吵得人不得安生。”
“小孩子都这样的,长大点就好了,睡眠规律了就好了。”楚砚溪顺势在长椅的另一端坐下,保持着既不显疏远又不具侵略性的安全距离。
注意到苏晚晴眉宇间那抹的疲惫,楚砚溪的心抽疼了一下:“带宝宝一定很辛苦吧?孩子爸爸不帮忙吗?”
“还好,他爸爸工作忙,经常加班、出差,在家时间少。不过,只要一有空,他就会帮忙带孩子,换尿布、冲奶粉都抢着做。”苏晚晴的语气里带着对丈夫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甚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维护。
可是,楚砚溪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那隐藏在一瞥一笑间的落寞与担忧。警察的妻子,尤其是一线刑警的妻子,注定要承受比常人更多的孤独、牵挂和提心吊胆。
两人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从带孩子的各种琐碎不易,聊到江城湿润宜人的气候与北方的干燥对比,又隐约提及各自的情况。
楚砚溪称自己是来江城投奔亲戚、暂时借住在此的毕业生,正在寻找工作机会,言语间流露出对教师职业的尊敬,以及对苏晚晴既能照顾年幼孩子又能兼顾工作的钦佩和不易。
苏晚晴似乎也很久没遇到能如此平和聊天的年轻女性,渐渐放下了心防。楚砚溪看着她温柔拍哄孩子的侧影,听着她带着吴语软侬口音的普通话,心中那份芥蒂,在真实、鲜活、充满温情的接触下,开始松动、瓦解。
此时的苏晚晴,是一位深爱着女儿的母亲,一位关心着丈夫的妻子,一个努力在家庭和工作中寻找平衡的普通女性。她深爱着怀中的婴儿,承担着家中大部分家务,还要为刑警丈夫的安危担忧。
楚砚溪发现,自己长久以来固化的怨恨,在此刻面对如此真实的母亲时,竟有些无处着落。
想到父亲未来的命运,楚砚溪话锋一转,神色变得郑重而略带一丝神秘,她稍稍压低了声音,确保只有两人能听清:“冒昧问一句,您爱人从事的工作是否有一定的危险性?”
苏晚晴微微一怔,眼神里多了些明显的探究和警惕,身体也坐直了些。
楚砚溪迎着她的目光,语气诚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请您别见怪,我家里以前有位长辈,是乡间有名的相士,懂些相面望气之术,我自幼跟着学了点皮毛。方才我观您面相,子女宫饱满红润,是福泽深厚、晚运亨通之相,但是……”
她刻意停顿了一下,加重了语气,“您的夫妻宫,也就是眉尾上方、靠近鬓角的位置,此处隐约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青暗之气,主夫君未来恐会遭遇一场不小的劫难,此劫与金属利器相关,煞气颇重,可能会有血光之灾,危及性命。”
苏晚晴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抱着孩子的手下意识地收紧。婴儿感受到母亲骤然紧张的情绪,不安地扭动了一下,发出一阵哼哼声。苏晚晴一边哄着孩子,一边不安地打量着楚砚溪。
作为刑警的妻子,她对这些话有着远超常人的敏感和恐惧,丈夫职业的高风险性是她内心深处最不敢触碰的噩梦。
楚砚溪连忙放缓语气,带着安抚的意味:“您先别怕!凡事有因必有果,有劫亦可有解。破解之法不是没有。”
她从口袋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早准备好的锦囊递了过去。这个锦囊用暗红色绸布缝制、正面用金线绣着个古朴的“福”字,看着很精致。
“这个锦囊请您收好,里面是一个八卦铜镜,能帮您爱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请放在您爱人的左侧口袋里,贴身收藏。切记!七年之后的冬天,也就是2005年冬至那天不要外出,只要那天安全度过,此后便是坦途。”
楚砚溪有过两次穿越的经验,知道只要自己离开,所有关于她的记忆都会消失。不管她提醒父亲多少次,他总会忘记。因此这一次,她决定送点实物。
楚砚溪心中暗自思忖,父亲是个2005年冬至那天被刺中腰部左侧,脾脏破裂而死。这个铜镜一来能够替父亲挡刀,二来能在一定程度上让母亲记起自己说过的话,从而影响未来的轨迹,增加父亲生还的可能。
苏晚晴打开那个不过巴掌大小的秀气锦囊,看到里面有一面迷你小铜镜,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她抬眼看看楚砚溪异常认真的眼眸,内心有些复杂。
理智告诉她这陌生姑娘说的一切太过离奇,应该立刻拒绝。可是,眼前这个姑娘眼神干净,语气诚恳,不带丝毫市侩之气,尤其是那句“与金属利器相关,恐有血光之灾”,引发了她内心最深的恐惧。
她想起了丈夫每次深夜出紧急现场时自己彻夜不眠的煎熬,想起了他警服袖口偶尔蹭上的、洗不净的暗红痕迹,想起了他轻描淡写带过的那些惊险瞬间……
楚砚溪微笑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不是?我不找您要钱,也不要您任何东西,不过是因为和您聊得开心,又看宝宝可爱,所以才想着结个善缘。”
苏晚晴迟疑了一会,最终还是将这个锦囊紧紧攥在手心:“谢谢……”
楚砚溪暗暗松了口气,一直紧绷的心弦稍缓:“不客气。对我而言,这不过是举手之劳,但对您而言,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人生。”
她顿了顿,仿佛不经意地将目光重新投向那个可爱的婴儿,语气轻松地问,“宝宝长得真好,她叫什么名字?”
苏晚晴低头看着怀中的女儿,眼神重新被无尽的温柔爱意填满,声音也柔和下来:“叫砚溪。砚是笔墨纸砚的砚,溪是溪流的溪。希望她将来能文秀聪颖,像溪水一样,清澈、坚韧,汇溪成河,百川入海,拥有开阔的人生。”
真是一个承载了父母美好期望的名字。
楚砚溪伸出手,虚虚地、极轻极轻地抚了抚婴儿娇嫩得仿佛透明的小脸蛋,动作轻柔得像是怕惊扰了一场易碎的梦。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只有自己能听见,却蕴含着跨越了漫长时光洪流的、无尽复杂的情绪,有怜爱,有遗憾,有告诫,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悲伤:
“小砚溪,好好爱爸爸,爱妈妈,也要……好好爱自己。”
这句话,既是说给眼前这个尚在襁褓、对未来一无所知的婴儿,又何尝不是对那个在家庭剧变中受伤、多年来封闭内心、从未真正学会与母亲和解、与过去和解、更不懂得如何好好爱自己的、成年后的楚砚溪的深切告诫与期盼?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匆匆从小区门口走来,是买菜归来的楚同裕。他看到妻子正和陌生姑娘说话,立刻快步走了过来,警觉地将目光投向楚砚溪。
“晚晴,怎么了?没事吧?”他语气关切,脚步沉稳,不动声色地挡在了妻女身前,目光锐利地扫过楚砚溪,带着职业性的审视。虽然年轻,但刑警的本能让他对任何接近家人的陌生人都保持着警惕。
苏晚晴连忙将锦囊紧紧攥在手心,下意识地藏到身后:“没事,这位姑娘路过,问了个路,我们……随便聊了几句。”她并不想让丈夫知道刚才那番关于“血光之灾”的谈话,怕增加他的心理负担。
楚同裕看了看面前这个气质沉静、眼神清澈坦荡的陌生姑娘,眉头微蹙,但见对方确实不像歹人,妻女也无恙,便没有再多问,只是对楚砚溪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他随即转过身,极其自然地俯身,从苏晚晴臂弯里接过女儿,脸上绽放出毫无阴霾的、灿烂如孩童般的笑容,语气宠溺:“小溪,有没有想爸爸?嗯?”
那一刻,夕阳的最后一抹金辉正好笼罩在这温馨的三口之家身上。
楚同裕高大的身躯微微弯着,形成一个保护性的姿态,苏晚晴仰头看着他,眼中满是依赖与柔情,怀中的婴儿似乎被父亲逗弄,发出咿呀的、模糊的音节。幸福、安宁、充满爱意的气息几乎要满溢出来。
楚砚溪静静地站着,看着这一家三口。
眼前的幸福景象美好得如同油画,灼烧着她的眼睛和心脏。泪水毫无预兆地涌上眼眶,视线也变得模糊起来。楚砚溪迅速低下头,用力眨眼,逼退那些泪水。
曾经,她也有一个如此幸福完满的家,也曾被父亲这样稳稳抱起,被母亲这样温柔凝视。
可是,命运的齿轮却在冷酷地转动着,眼前这一切会消失、曾经的爱会转移、所有幸福都会荡然无存。只希望,她今天所做的一切,能够对抗那不公的命运,能够让眼前这一切美好永远延续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楚砚溪此刻内心酸楚无比。对命运无常的深切悲恸、对逝去幸福的锥心追忆,以及一种巨大的、无法融入的孤独感,种种强烈的情绪涌上心头,楚砚溪低声道了句再见,匆匆转身,快步走开。
走出很远,直到拐过街角,再也看不到那栋楼,楚砚溪才敢停下脚步,靠在冰凉的墙壁上,仰起头,深深呼吸着傍晚微凉的空气,试图平复汹涌的心潮。
夜幕开始降临,华灯初上。
江城师范大学教职工小区三楼那扇窗户里,温暖的灯光依旧亮着,隐约传来婴儿的啼哭和大人温柔的安抚声,那是人间最平凡的烟火气,也是楚砚溪此生无法再触及的遥远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