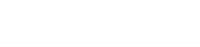楚砚溪将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为的就是减少对方的戒心。
听她说所求不过活命,老刀不由得点了点头。他转卖过不少嫩货,拐过来时花朵正艳,不过几年便折腾得只剩一条命。越是有文化的,越是烈性,楚砚溪说的倒是真心话。
楚砚溪见他动容,继续加码:“计划成功前,我和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东西做不出来,或者效果不好,第一个死的是我。至于保证……你可以给我上脚铐,派人看着我制作,原料由你控制,我只负责技术和配比。成功了,我们按功劳分钱;失败了,你随时可以处置我。”
楚砚溪停顿片刻,自嘲一笑:“毕竟,只要我清白还在,就能值五千块,不过就是晚几天卖出去而已,是不是?”
老刀沉默了,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门框,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权衡。楚砚溪没有说错,一个有真本事、且生死由他掌控的技术人才,比一个一次性卖五千块的货物,价值高得多。如果楚砚溪骗他,大不了再卖一次好了。老刀就不信,她还能跑得出榆树台!
楚砚溪趁热打铁,将话题转回到陆哲身上:“至于他……赵家屯文化站那边一旦联系不上,肯定会和市里文化局那边联系,询问他的去向与行程。一个市里来的干部失踪不是小事,万一公安沿着他乘坐的火车车次查过来,你们这条经营已久的铁路线就废了。损失有多大,刀哥你比我清楚。”
老刀眉头紧锁,这确实是他一直担心的问题。
楚砚溪瞥了地上“昏迷”的陆哲一眼:“这样,我帮你们出个主意,算是合作之前我的诚意。”
老刀眼睛一亮:“你说。”
楚砚溪:“先别杀他。让他明天一早打电话稳住赵家屯文化站和清源县文化局那边,就说水土不服病了,需要静养一段时间,或者考察任务延长,拖上一两个月。”
老刀沉吟半晌,没有说话。眼前这女人每一句话都说到了他的心坎里,真不愧是读过书的大学生。
她说的没错,穿橙色夹克这小子放在手里真是块烫手的山芋!杀了吧,怕公安那边查过来;不杀吧,白养个废物,划不来。
“做炸药过程很复杂,我需要一个助手。正好他是个文化人,这段时间先给我帮忙。等我们的大事办成,拿到足够的钱,到时候再处理他,或者把他往深山里一扔,制造个意外失足的现场,神不知鬼不觉,岂不更稳妥?既能消除眼前风险,又能为我们的大事争取时间。”
楚砚溪提的这个方案考虑很周全,完全从老刀的利益和风险控制角度出发,将陆哲从“无用的麻烦”变成了一个“可暂时利用的资产”。其老谋深算的程度,让老刀都暗自心惊,更让地上装死的陆哲听得五味杂陈。
他是个律师,敏锐的观察力、共情与协作、法庭上的心理攻防……这些都是他的专业素养。但作为一名离婚律师,他更擅长的,是法律范围之内的博弈,是家庭矛盾与纠纷的处理。
落入人贩子手中的他,有一种秀才遇到兵、虎落平阳的无力感。
没想到,曾经被他评价为“无情机器”的楚砚溪,却在这场困局中利用她智慧与能力,为他争来了一线生机。
老刀盯着楚砚溪,看了足足有一分钟,仿佛要透过她这张漂亮的脸蛋看清她脑子里到底还装着多少奇怪的、却又让他心动的点子。
最终,他咧开嘴,露出一个混合着残忍、兴奋和一丝赏识的狰狞笑容:“好!好!有点意思!真他娘的有意思!老妹儿,你确实和那些哭哭啼啼的货色不一样。老子就信你一回,陪你玩这把大的!要是赢了,以后跟我吃香喝辣;要是敢耍花招……”
他后面的话没说完,但那股冰冷的杀意让空气都几乎凝固。
“我人都在你手里,能耍什么花样?”楚砚溪坦然地看着他,再次强调,“合作,是双赢。你得到钱和江湖地位,我得到活下去的机会,很公平。”
“成交!”老刀又踢了一脚陆哲,“这小子先留着,捆结实点!”
他扫了一眼角落里昏迷不醒的女孩们,眸光阴冷,像看三个死人。在他看来,这三个女孩迟早都是要卖到深山里去的。到了那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什么消息也传递不出去,老刀根本不在乎她们到底听没听见、会不会告密。
老刀转身走出土坯房,对看守低声吩咐了几句,重点是看好楚砚溪和陆哲,暂时满足楚砚溪的基本需求,但要加强看守。
门被重新锁上,沉重的铁锁撞击声在夜里格外刺耳。
门一关,土坯房内再次陷入死寂。
陆哲这才敢悄悄睁开眼,在极致的黑暗中望向楚砚溪的方向。他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挺直的轮廓,仿佛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谈判,和去菜场买颗大白菜一样,都是小事儿。
楚砚溪看不到陆哲的脸,但从他越来越快的心跳声感受到了他那复杂的内心。她没有任何解释,只是缓缓地靠回冰冷的墙壁,闭上眼,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低语:“活下去,才有机会谈正义。现在,睡觉,保存体力。”
她的语气依旧平静。
陆哲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楚砚溪那份令人敬畏的职业背后,隐藏着一种近乎非人的理智、钢铁般的意志和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坚定与执着。
作者有话说:
----------------------
第7章 质疑 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
不知过了多久,门外再次传来脚步声和开锁的“哗啦”声。
门被推开,看守粗哑的嗓音响起:“你,还有那个半死的,出来!刀哥给你们换地方!”
手电光柱扫过,落在楚砚溪和陆哲身上。楚砚溪缓缓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因长时间捆绑而麻木的手腕,神情平静。陆哲看到楚砚溪站了起来,也跟着慢慢起身,和她一起走出这间充满霉味的土坯房。
看守似乎得到了老刀的特别吩咐,虽然态度依旧粗暴,但没有再动手动脚。
就在他们即将迈出门槛的刹那,角落里那个一直将头埋在臂弯、一声不吭的女孩,眼中突然爆发出一种绝望的光芒。她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猛地扑了过来,死死抱住楚砚溪的小腿,声音嘶哑地哀求:“姐!姐!带我走!求求你,带我一起走!别把我留在这儿!求你了!”
她的动作太快,太突然,带着一种濒临崩溃的决绝。楚砚溪的身体瞬间僵住,她能清晰地感受到女孩身体的剧烈颤抖和紧抱住她小腿的力度。
看守骂了一句,上前就要拉扯。
楚砚溪却先开了口,声音干涩:“松开。”
女孩像是没听见,抱得更紧,眼泪和鼻涕糊在楚砚溪的裤脚上,语无伦次地哀求:“带我走吧,我不要卖给人当老婆!我能干活,我不跑,别丢下我……”
楚砚溪压住心底翻涌的情绪,再次低声道:“松开!”她此刻自身难保,能暂且救下陆哲的小命已是极致,哪里还能带一个陌生女孩?
她的拒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女孩眼中最后一点火光。女孩的手臂无力地滑落,瘫坐在地上,发出压抑到极致的、如同小兽般的呜咽。
一旁的陆哲心中似有火烧,他有心想要多说几句,但也知道此刻只能拒绝。他忍着后脑的剧痛,借着门外灯光,认真看着那个女孩,努力记下她的容貌与特征。
女孩察觉到了他的目光,抬起泪眼朦胧的脸,像是抓住了一丝微弱的希望,喃喃重复着:“我叫魏艳丽,我叫魏艳丽……”
“妈的!不服管的狗东西!”看守早已不耐烦,猛地一把粗暴地将女孩推开。
女孩瘦弱的身体撞在冰冷的土墙上,发出一声闷响和痛呼。紧接着,看守反手就狠狠抽了她一耳光!
“啪!”
清脆的响声在黑暗中格外刺耳。
明明被打的是那个叫魏艳丽的女孩,可是陆哲却不自觉地脑袋一偏,仿佛被打的是他,甚至连脸颊都能感觉到那火辣辣地疼痛。
“再他妈废话,老子现在就弄死你!”看守恶狠狠地踹了魏艳丽一脚。
楚砚溪伸出手,用力拽了陆哲一把:“走!”
陆哲最后看了一眼墙角那个再次陷入绝望、连哭泣都不敢出声的女孩,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和悲愤涌上心头。但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咬紧牙关,踉跄着走出这间令人窒息的土坯房。
院子里的空气依然浑浊,但比屋内的浓浓霉味要好上一些。夜空漆黑,只有正房窗户透出一点昏黄的光。看守领着他们走向院子东侧另一间稍小的土坯房,推开门,里面同样简陋,但显然比之前那间没有窗户的屋子要好上不少。
墙上有一扇小窗户,窗户装着木栅格,糊了窗纸。地上铺着干草,有一张用木板和砖头搭成的简易床铺,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看不出原本颜色的褥子。角落里放着一个破旧的木桶,似乎是便桶。虽然依旧破败,但至少有了基本的生活设施,而且相对干净。
“刀哥说了,让你们暂时睡在这里。安分点,别耍花样!”看守恶声恶气地丢下这句话,又扔进来一个粗陶水壶和两个粗糙的、看起来硬邦邦的玉米面馍馍,“吃的喝的给了,别他娘的再嚷嚷!”
门再次被关上,但这一次,空间不再是完全的黑暗,小窗透进些许微弱的星光,让人能勉强视物。
陆哲直到门外脚步声远去,才真正松了口气,挣扎着靠墙坐起,后脑的伤处还在隐隐作痛。他看着地上的水壶和馍馍,喉咙干得发紧。
楚砚溪走过去,拿起水壶,晃了晃,又凑近闻了一下,确认只是普通的井水后才递给陆哲:“先喝点水,慢点喝。”
她的动作自然,带着一种习惯性的谨慎。陆哲接过水壶,贪婪地喝了几大口,冰凉的水划过喉咙,暂时压下了那股灼烧感。
楚砚溪又将一个馍馍递给他。馍馍又硬又糙,剌嗓子,但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依旧是宝贵的能量来源。
陆哲默默地啃着,味同嚼蜡。
吃完东西,体力稍微恢复了一些。两人看着房间里唯一的那张床,气氛有些尴尬。
“你睡床吧。”陆哲几乎是下意识地开口,声音还有些沙哑,“我……我睡地上就行。”他的绅士风度与良好教养让他做出了这个选择。
楚砚溪看了他一眼:“床不大,挤一挤能睡。”
她的语气没有任何暧昧或犹豫。在这种朝不保夕的环境里,无谓的谦让和矜持都是奢侈且危险的。
陆哲愣了一下,没有再坚持,点了点头。
两人和衣躺在那张简陋的板床上,背对着背。床板很硬,褥子薄得几乎感觉不到,彼此都能感受到对方身体传来的微弱热量和紧绷的肌肉线条。这是一种极其诡异而亲密的情景,但此刻充斥其中的,只有沉重的生存压力和未散的惊悸。
狭小的空间里,彼此的呼吸声清晰可闻。
沉默了很久,陆哲终于忍不住,用极低的气声,问出了那个一直压在他心头、沉甸甸的问题:“那……那三个女孩会怎么样?”
他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难过和愧疚。他们暂时获得了安全,但那三个同样被拐来的女孩,却被留在了那间土坯房里,命运未卜。
楚砚溪睡在内侧,睁开眼看着斑驳的墙壁:“能活下来。”
陆哲看着小小的、装了木栅格的窗户:“可是……”
楚砚溪打断他的话:“活着,才是王道。”作为一名谈判专家,她将“生命至上”这个理念深深刻在脑海中。
冲动盲目、轻举妄动,结果只有一个——大家一起死。
楚砚溪与老刀谈判的目的,是先争取自己与陆哲能活下来,取得老刀的初步信任,等时机成熟,再端掉他们这个人口贩卖团伙。
只有她先活下来,才能救更多的人,包括那三个被拐来的女孩。她们一个叫杨娟,一个叫小菊,还有一个叫魏艳丽。
陆哲知道楚砚溪说的是事实,是当前情况下最理性的选择,但他心里却难过至极。他脑海里不断闪过那三个女孩惊恐无助的眼神,那个腿折女孩压抑的痛哼。
“她们,她们的未来……”陆哲的声音有压不住的沉重,“就算以后得救,经历这些,也毁了。”
“活着,才有未来。”与刀哥斗智斗勇这么久,楚砚溪早就又累又困,虽然她很不想说话,但她听得出来陆哲内心的纠结,认真解释着。
从她以前与陆哲打交道的经验,陆哲这人道德感很强,同情心泛滥,处理离婚案件不管谁是谁非,一定会无条件地偏向女性。他对女性的痛苦有一种近乎执拗的同情,只要是女性诉说婚姻中的不幸,他都会站在她们这一边,为她们争取最大的权益。
“只要不主动寻死,她们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人贩子卖她们是为了赚钱,买家买她们是为了传宗接代或劳动力,在达到目的前,不会轻易要她们的命。”
听了楚砚溪的话,陆哲自心底涌上一种深深的痛楚:“那清白呢?尊严呢?这些东西,在她们以后的人生里,就不重要了吗?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
有些伤害,是刻在灵魂里的,终身无法磨灭。
——这是他作为律师,在处理无数婚姻、家庭案件,尤其是那些遭受巨大创伤的女性案件时,最深切的体会。
楚砚溪的背影僵了僵,没有马上说话。
这也是她所困惑的地方——她与张雅的谈判为什么会失败?张雅为了那个渣男,宁可付出生命,值得吗?就算王鹏不爱她,她还有女儿,还有未来漫长的人生要走,为什么要选择自爆那么绝决的告别方式?
在张雅的心里,对婚姻的忠诚比生命更为重要吗?
狭小的空间里,只剩下两人沉重而压抑的呼吸声。窗外,远远传来几声犬吠,更衬得这夜寂静得可怕。
良久,良久,楚砚溪极其缓慢地,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一句:
“除生死,无大事。”
这句话,轻得像叹息,却让陆哲心中一颤。
只有活下去,才有机会,让“清白”和“尊严”这些词汇,变得有意义。
陆哲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他最终什么也没能说。
楚砚溪睁着眼,望着墙壁上斑驳的、在微光下隐约可见的霉斑,脑子里依然浮现着张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眼睛里那一抹平静的绝决。
作者有话说:
听她说所求不过活命,老刀不由得点了点头。他转卖过不少嫩货,拐过来时花朵正艳,不过几年便折腾得只剩一条命。越是有文化的,越是烈性,楚砚溪说的倒是真心话。
楚砚溪见他动容,继续加码:“计划成功前,我和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东西做不出来,或者效果不好,第一个死的是我。至于保证……你可以给我上脚铐,派人看着我制作,原料由你控制,我只负责技术和配比。成功了,我们按功劳分钱;失败了,你随时可以处置我。”
楚砚溪停顿片刻,自嘲一笑:“毕竟,只要我清白还在,就能值五千块,不过就是晚几天卖出去而已,是不是?”
老刀沉默了,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门框,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权衡。楚砚溪没有说错,一个有真本事、且生死由他掌控的技术人才,比一个一次性卖五千块的货物,价值高得多。如果楚砚溪骗他,大不了再卖一次好了。老刀就不信,她还能跑得出榆树台!
楚砚溪趁热打铁,将话题转回到陆哲身上:“至于他……赵家屯文化站那边一旦联系不上,肯定会和市里文化局那边联系,询问他的去向与行程。一个市里来的干部失踪不是小事,万一公安沿着他乘坐的火车车次查过来,你们这条经营已久的铁路线就废了。损失有多大,刀哥你比我清楚。”
老刀眉头紧锁,这确实是他一直担心的问题。
楚砚溪瞥了地上“昏迷”的陆哲一眼:“这样,我帮你们出个主意,算是合作之前我的诚意。”
老刀眼睛一亮:“你说。”
楚砚溪:“先别杀他。让他明天一早打电话稳住赵家屯文化站和清源县文化局那边,就说水土不服病了,需要静养一段时间,或者考察任务延长,拖上一两个月。”
老刀沉吟半晌,没有说话。眼前这女人每一句话都说到了他的心坎里,真不愧是读过书的大学生。
她说的没错,穿橙色夹克这小子放在手里真是块烫手的山芋!杀了吧,怕公安那边查过来;不杀吧,白养个废物,划不来。
“做炸药过程很复杂,我需要一个助手。正好他是个文化人,这段时间先给我帮忙。等我们的大事办成,拿到足够的钱,到时候再处理他,或者把他往深山里一扔,制造个意外失足的现场,神不知鬼不觉,岂不更稳妥?既能消除眼前风险,又能为我们的大事争取时间。”
楚砚溪提的这个方案考虑很周全,完全从老刀的利益和风险控制角度出发,将陆哲从“无用的麻烦”变成了一个“可暂时利用的资产”。其老谋深算的程度,让老刀都暗自心惊,更让地上装死的陆哲听得五味杂陈。
他是个律师,敏锐的观察力、共情与协作、法庭上的心理攻防……这些都是他的专业素养。但作为一名离婚律师,他更擅长的,是法律范围之内的博弈,是家庭矛盾与纠纷的处理。
落入人贩子手中的他,有一种秀才遇到兵、虎落平阳的无力感。
没想到,曾经被他评价为“无情机器”的楚砚溪,却在这场困局中利用她智慧与能力,为他争来了一线生机。
老刀盯着楚砚溪,看了足足有一分钟,仿佛要透过她这张漂亮的脸蛋看清她脑子里到底还装着多少奇怪的、却又让他心动的点子。
最终,他咧开嘴,露出一个混合着残忍、兴奋和一丝赏识的狰狞笑容:“好!好!有点意思!真他娘的有意思!老妹儿,你确实和那些哭哭啼啼的货色不一样。老子就信你一回,陪你玩这把大的!要是赢了,以后跟我吃香喝辣;要是敢耍花招……”
他后面的话没说完,但那股冰冷的杀意让空气都几乎凝固。
“我人都在你手里,能耍什么花样?”楚砚溪坦然地看着他,再次强调,“合作,是双赢。你得到钱和江湖地位,我得到活下去的机会,很公平。”
“成交!”老刀又踢了一脚陆哲,“这小子先留着,捆结实点!”
他扫了一眼角落里昏迷不醒的女孩们,眸光阴冷,像看三个死人。在他看来,这三个女孩迟早都是要卖到深山里去的。到了那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什么消息也传递不出去,老刀根本不在乎她们到底听没听见、会不会告密。
老刀转身走出土坯房,对看守低声吩咐了几句,重点是看好楚砚溪和陆哲,暂时满足楚砚溪的基本需求,但要加强看守。
门被重新锁上,沉重的铁锁撞击声在夜里格外刺耳。
门一关,土坯房内再次陷入死寂。
陆哲这才敢悄悄睁开眼,在极致的黑暗中望向楚砚溪的方向。他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挺直的轮廓,仿佛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谈判,和去菜场买颗大白菜一样,都是小事儿。
楚砚溪看不到陆哲的脸,但从他越来越快的心跳声感受到了他那复杂的内心。她没有任何解释,只是缓缓地靠回冰冷的墙壁,闭上眼,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低语:“活下去,才有机会谈正义。现在,睡觉,保存体力。”
她的语气依旧平静。
陆哲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楚砚溪那份令人敬畏的职业背后,隐藏着一种近乎非人的理智、钢铁般的意志和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坚定与执着。
作者有话说:
----------------------
第7章 质疑 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
不知过了多久,门外再次传来脚步声和开锁的“哗啦”声。
门被推开,看守粗哑的嗓音响起:“你,还有那个半死的,出来!刀哥给你们换地方!”
手电光柱扫过,落在楚砚溪和陆哲身上。楚砚溪缓缓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因长时间捆绑而麻木的手腕,神情平静。陆哲看到楚砚溪站了起来,也跟着慢慢起身,和她一起走出这间充满霉味的土坯房。
看守似乎得到了老刀的特别吩咐,虽然态度依旧粗暴,但没有再动手动脚。
就在他们即将迈出门槛的刹那,角落里那个一直将头埋在臂弯、一声不吭的女孩,眼中突然爆发出一种绝望的光芒。她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猛地扑了过来,死死抱住楚砚溪的小腿,声音嘶哑地哀求:“姐!姐!带我走!求求你,带我一起走!别把我留在这儿!求你了!”
她的动作太快,太突然,带着一种濒临崩溃的决绝。楚砚溪的身体瞬间僵住,她能清晰地感受到女孩身体的剧烈颤抖和紧抱住她小腿的力度。
看守骂了一句,上前就要拉扯。
楚砚溪却先开了口,声音干涩:“松开。”
女孩像是没听见,抱得更紧,眼泪和鼻涕糊在楚砚溪的裤脚上,语无伦次地哀求:“带我走吧,我不要卖给人当老婆!我能干活,我不跑,别丢下我……”
楚砚溪压住心底翻涌的情绪,再次低声道:“松开!”她此刻自身难保,能暂且救下陆哲的小命已是极致,哪里还能带一个陌生女孩?
她的拒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女孩眼中最后一点火光。女孩的手臂无力地滑落,瘫坐在地上,发出压抑到极致的、如同小兽般的呜咽。
一旁的陆哲心中似有火烧,他有心想要多说几句,但也知道此刻只能拒绝。他忍着后脑的剧痛,借着门外灯光,认真看着那个女孩,努力记下她的容貌与特征。
女孩察觉到了他的目光,抬起泪眼朦胧的脸,像是抓住了一丝微弱的希望,喃喃重复着:“我叫魏艳丽,我叫魏艳丽……”
“妈的!不服管的狗东西!”看守早已不耐烦,猛地一把粗暴地将女孩推开。
女孩瘦弱的身体撞在冰冷的土墙上,发出一声闷响和痛呼。紧接着,看守反手就狠狠抽了她一耳光!
“啪!”
清脆的响声在黑暗中格外刺耳。
明明被打的是那个叫魏艳丽的女孩,可是陆哲却不自觉地脑袋一偏,仿佛被打的是他,甚至连脸颊都能感觉到那火辣辣地疼痛。
“再他妈废话,老子现在就弄死你!”看守恶狠狠地踹了魏艳丽一脚。
楚砚溪伸出手,用力拽了陆哲一把:“走!”
陆哲最后看了一眼墙角那个再次陷入绝望、连哭泣都不敢出声的女孩,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和悲愤涌上心头。但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咬紧牙关,踉跄着走出这间令人窒息的土坯房。
院子里的空气依然浑浊,但比屋内的浓浓霉味要好上一些。夜空漆黑,只有正房窗户透出一点昏黄的光。看守领着他们走向院子东侧另一间稍小的土坯房,推开门,里面同样简陋,但显然比之前那间没有窗户的屋子要好上不少。
墙上有一扇小窗户,窗户装着木栅格,糊了窗纸。地上铺着干草,有一张用木板和砖头搭成的简易床铺,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看不出原本颜色的褥子。角落里放着一个破旧的木桶,似乎是便桶。虽然依旧破败,但至少有了基本的生活设施,而且相对干净。
“刀哥说了,让你们暂时睡在这里。安分点,别耍花样!”看守恶声恶气地丢下这句话,又扔进来一个粗陶水壶和两个粗糙的、看起来硬邦邦的玉米面馍馍,“吃的喝的给了,别他娘的再嚷嚷!”
门再次被关上,但这一次,空间不再是完全的黑暗,小窗透进些许微弱的星光,让人能勉强视物。
陆哲直到门外脚步声远去,才真正松了口气,挣扎着靠墙坐起,后脑的伤处还在隐隐作痛。他看着地上的水壶和馍馍,喉咙干得发紧。
楚砚溪走过去,拿起水壶,晃了晃,又凑近闻了一下,确认只是普通的井水后才递给陆哲:“先喝点水,慢点喝。”
她的动作自然,带着一种习惯性的谨慎。陆哲接过水壶,贪婪地喝了几大口,冰凉的水划过喉咙,暂时压下了那股灼烧感。
楚砚溪又将一个馍馍递给他。馍馍又硬又糙,剌嗓子,但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依旧是宝贵的能量来源。
陆哲默默地啃着,味同嚼蜡。
吃完东西,体力稍微恢复了一些。两人看着房间里唯一的那张床,气氛有些尴尬。
“你睡床吧。”陆哲几乎是下意识地开口,声音还有些沙哑,“我……我睡地上就行。”他的绅士风度与良好教养让他做出了这个选择。
楚砚溪看了他一眼:“床不大,挤一挤能睡。”
她的语气没有任何暧昧或犹豫。在这种朝不保夕的环境里,无谓的谦让和矜持都是奢侈且危险的。
陆哲愣了一下,没有再坚持,点了点头。
两人和衣躺在那张简陋的板床上,背对着背。床板很硬,褥子薄得几乎感觉不到,彼此都能感受到对方身体传来的微弱热量和紧绷的肌肉线条。这是一种极其诡异而亲密的情景,但此刻充斥其中的,只有沉重的生存压力和未散的惊悸。
狭小的空间里,彼此的呼吸声清晰可闻。
沉默了很久,陆哲终于忍不住,用极低的气声,问出了那个一直压在他心头、沉甸甸的问题:“那……那三个女孩会怎么样?”
他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难过和愧疚。他们暂时获得了安全,但那三个同样被拐来的女孩,却被留在了那间土坯房里,命运未卜。
楚砚溪睡在内侧,睁开眼看着斑驳的墙壁:“能活下来。”
陆哲看着小小的、装了木栅格的窗户:“可是……”
楚砚溪打断他的话:“活着,才是王道。”作为一名谈判专家,她将“生命至上”这个理念深深刻在脑海中。
冲动盲目、轻举妄动,结果只有一个——大家一起死。
楚砚溪与老刀谈判的目的,是先争取自己与陆哲能活下来,取得老刀的初步信任,等时机成熟,再端掉他们这个人口贩卖团伙。
只有她先活下来,才能救更多的人,包括那三个被拐来的女孩。她们一个叫杨娟,一个叫小菊,还有一个叫魏艳丽。
陆哲知道楚砚溪说的是事实,是当前情况下最理性的选择,但他心里却难过至极。他脑海里不断闪过那三个女孩惊恐无助的眼神,那个腿折女孩压抑的痛哼。
“她们,她们的未来……”陆哲的声音有压不住的沉重,“就算以后得救,经历这些,也毁了。”
“活着,才有未来。”与刀哥斗智斗勇这么久,楚砚溪早就又累又困,虽然她很不想说话,但她听得出来陆哲内心的纠结,认真解释着。
从她以前与陆哲打交道的经验,陆哲这人道德感很强,同情心泛滥,处理离婚案件不管谁是谁非,一定会无条件地偏向女性。他对女性的痛苦有一种近乎执拗的同情,只要是女性诉说婚姻中的不幸,他都会站在她们这一边,为她们争取最大的权益。
“只要不主动寻死,她们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人贩子卖她们是为了赚钱,买家买她们是为了传宗接代或劳动力,在达到目的前,不会轻易要她们的命。”
听了楚砚溪的话,陆哲自心底涌上一种深深的痛楚:“那清白呢?尊严呢?这些东西,在她们以后的人生里,就不重要了吗?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
有些伤害,是刻在灵魂里的,终身无法磨灭。
——这是他作为律师,在处理无数婚姻、家庭案件,尤其是那些遭受巨大创伤的女性案件时,最深切的体会。
楚砚溪的背影僵了僵,没有马上说话。
这也是她所困惑的地方——她与张雅的谈判为什么会失败?张雅为了那个渣男,宁可付出生命,值得吗?就算王鹏不爱她,她还有女儿,还有未来漫长的人生要走,为什么要选择自爆那么绝决的告别方式?
在张雅的心里,对婚姻的忠诚比生命更为重要吗?
狭小的空间里,只剩下两人沉重而压抑的呼吸声。窗外,远远传来几声犬吠,更衬得这夜寂静得可怕。
良久,良久,楚砚溪极其缓慢地,用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一句:
“除生死,无大事。”
这句话,轻得像叹息,却让陆哲心中一颤。
只有活下去,才有机会,让“清白”和“尊严”这些词汇,变得有意义。
陆哲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他最终什么也没能说。
楚砚溪睁着眼,望着墙壁上斑驳的、在微光下隐约可见的霉斑,脑子里依然浮现着张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眼睛里那一抹平静的绝决。
作者有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