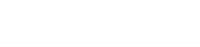渾英沒理我,笑了笑︰“五郎,你可是听說了我這舊人如今身陷危難,故而來助我的麼?”
她話里譏諷的意味很濃,安重璋卻像沒听出似的,沉聲道︰“你若有什麼吩咐,我自是盡力。”
渾英嗤笑道︰“突厥俗話說,‘婦人舍去恩愛而使自己頭腦輕快’。我舍去和你的恩愛,頭腦輕快多了,倒也沒什麼要你相助的事。”
眼見得他們兩個說不下去,我斂衽向渾英行禮︰“我今日來尋渾娘子,原是有幾句話請教。”
“你盡可以說,我卻未必要答。”渾英解下腰間的酒囊,喝了兩口,抹掉唇邊的酒漬。
安重璋嘆道︰“這位小娘子是朝廷左丞相的女兒,阿英,你……”
“涼州天高地迥,朝廷遠在千里之外,我不識得什麼左丞相。就連崔常侍,我也不見得便要害怕。”渾英抬頭望天,撢了撢袍子,舉動間滿是厭惡。
我清了清嗓子,換成了突厥語,正容道︰“崔常侍為人厚道,澤被河西軍民。渾娘子,你不喜他,可是有什麼委屈?”
渾英似是沒想到我會說突厥話,也沒想到我會這麼問她,怔了片刻,神情微轉柔和︰“我有一弟不幸流落吐蕃。”
只這一句話,我恍然大悟。邊境重燃戰火,流落吐蕃的漢地商人多半遭際堪憂,難怪她對與吐蕃開戰的崔希逸一副反感的樣子。
我點首道︰“我明白了。你阿弟為何去了吐蕃?”
“阿弟想要買入他們的金器,帶回涼州,再販到隴右和兩京。”渾英皺著眉頭,又灌了一口酒。
其時吐蕃金器以冶制精巧而聞名,吐蕃與大唐貿易時,向大唐販售金銀器者不在少數。我思索道︰“原來你們也做吐蕃的生意。”
渾英道︰“這不是很尋常的事嗎?便是他安郎不也一樣?他家世代善養名馬,難道便不買青海馬,不買吐蕃的戰馬?”
她這話倒也有理。我還欲再問時,忽有幾個人自旁邊的斜街繞出,氣勢洶洶地沖了過來,口中喊著︰“我們信了渾家的名號,才從你手里買了布,你卻遲遲拿不出來!”“我們等著這些布匹,是要給邊軍健兒們做冬衣的!我們如何向健兒們交代!”“還沒有冬衣穿,健兒們只怕要凍死,談什麼保家衛國!”
渾英見勢,大聲道︰“請你們再寬限幾日,我……”孰料最前面的那個商人一把抓住了她,叫嚷道︰“還我們錢來!”緊接著又有兩個商人沖向她,抓住她的手臂,高喊︰“拿不出布匹,就還我們錢!用玉料和寶石來抵!”渾英一時又驚又怒,十分狼狽。
“且慢!”安重璋大喝一聲,“住手!”
幾人為他威儀所震,怔了數息,隨即又喧嚷道︰“你是誰!”“我們已尋了專司集市的官長!是官長許我們來向她討債的!”
“我是渾英的友人。”安重璋平靜道。
那一瞬間,我看到站在台階上的渾英眼里閃過一絲失落。
安重璋又道︰“我姓安,名重璋。你們要什麼,盡可向我來討。”商人們想是听過他的名號,立即扯住他討要說法。
我被擠到一邊,只能苦笑︰看來渾英破產屬實,只怕也沒有能力賄賂中使。那麼,剩下的便只有那個姓阿史那的商人了?
安重璋初步替渾英料理了欠下的賬,才喊上我離開。渾英在背後叫住他,頓了頓,才道︰“多謝。”安重璋嘆了口氣,只溫聲道︰“你多叫幾個族人來和你同住罷。再有這樣的事,你就來尋我。”
邊地的秋日沒有太多暖意,卻有足夠濃郁的色彩。遠處祁連山頂的雪色連著雲色,在陽光映照下,亮得極具侵略性,簡直有些刺目。安重璋望著那片白亮的雪和雲,閉了閉眼,低聲道︰“我和渾英有過婚約。”
我頷首,一個是鐵勒族人,一個是九姓胡人之後,這種外族婚姻很常見。
“阿英……她實則不喜漢人,也不敬重大唐皇帝。她說,渾部內附大唐,已有數代,可唐人仍然不肯像待漢人一樣待渾部的族人……河西各族混居,邊民有這般心思,也不足為奇。但……自從我曾祖涼國公起,我家一直忠于大唐皇帝。我很敬愛她,但又實在為難。”他說得委婉,但話中的無奈之意掩也掩不住。
渾英不能接受被區別對待,這其實是很多胡人都有的感受。而安重璋家是河西豪族,屬于本地長官也要著意禮敬的地方大豪。他的曾祖安興貴是凌煙閣功臣,到了他父親這輩,雖不如曾祖風采閃耀,也曾做過鄯州都督,所以他是真正的土豪,又是官二代,沒法代入渾英的情緒,也很自然。
政見不合導致的分手,一般是無法挽回的。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也或許他根本不需要安慰,于是我只能向路邊的餅販買了一個加糖的餅,塞給他。
我們約了過一日去尋阿史那盈科,便分開了。見時辰尚早,我便迫不及待地去尋王維。王維聞得我來訪,連忙迎了出來。我故意挑刺道︰“你並非倒屣相迎,可見心中不甚以我為意。”
他喊冤︰“你只管胡白!我寫字寫到一半,且放下了來迎你。”我一顧他身上,果見他袖口處微染墨漬,遂笑道︰“你寫的什麼字?”王維笑道︰“是一首詩。我正在苦思其中二字。”領我走入室中,指向案上鋪開的熟紙。我看時,只見那紙上寫的是︰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
她話里譏諷的意味很濃,安重璋卻像沒听出似的,沉聲道︰“你若有什麼吩咐,我自是盡力。”
渾英嗤笑道︰“突厥俗話說,‘婦人舍去恩愛而使自己頭腦輕快’。我舍去和你的恩愛,頭腦輕快多了,倒也沒什麼要你相助的事。”
眼見得他們兩個說不下去,我斂衽向渾英行禮︰“我今日來尋渾娘子,原是有幾句話請教。”
“你盡可以說,我卻未必要答。”渾英解下腰間的酒囊,喝了兩口,抹掉唇邊的酒漬。
安重璋嘆道︰“這位小娘子是朝廷左丞相的女兒,阿英,你……”
“涼州天高地迥,朝廷遠在千里之外,我不識得什麼左丞相。就連崔常侍,我也不見得便要害怕。”渾英抬頭望天,撢了撢袍子,舉動間滿是厭惡。
我清了清嗓子,換成了突厥語,正容道︰“崔常侍為人厚道,澤被河西軍民。渾娘子,你不喜他,可是有什麼委屈?”
渾英似是沒想到我會說突厥話,也沒想到我會這麼問她,怔了片刻,神情微轉柔和︰“我有一弟不幸流落吐蕃。”
只這一句話,我恍然大悟。邊境重燃戰火,流落吐蕃的漢地商人多半遭際堪憂,難怪她對與吐蕃開戰的崔希逸一副反感的樣子。
我點首道︰“我明白了。你阿弟為何去了吐蕃?”
“阿弟想要買入他們的金器,帶回涼州,再販到隴右和兩京。”渾英皺著眉頭,又灌了一口酒。
其時吐蕃金器以冶制精巧而聞名,吐蕃與大唐貿易時,向大唐販售金銀器者不在少數。我思索道︰“原來你們也做吐蕃的生意。”
渾英道︰“這不是很尋常的事嗎?便是他安郎不也一樣?他家世代善養名馬,難道便不買青海馬,不買吐蕃的戰馬?”
她這話倒也有理。我還欲再問時,忽有幾個人自旁邊的斜街繞出,氣勢洶洶地沖了過來,口中喊著︰“我們信了渾家的名號,才從你手里買了布,你卻遲遲拿不出來!”“我們等著這些布匹,是要給邊軍健兒們做冬衣的!我們如何向健兒們交代!”“還沒有冬衣穿,健兒們只怕要凍死,談什麼保家衛國!”
渾英見勢,大聲道︰“請你們再寬限幾日,我……”孰料最前面的那個商人一把抓住了她,叫嚷道︰“還我們錢來!”緊接著又有兩個商人沖向她,抓住她的手臂,高喊︰“拿不出布匹,就還我們錢!用玉料和寶石來抵!”渾英一時又驚又怒,十分狼狽。
“且慢!”安重璋大喝一聲,“住手!”
幾人為他威儀所震,怔了數息,隨即又喧嚷道︰“你是誰!”“我們已尋了專司集市的官長!是官長許我們來向她討債的!”
“我是渾英的友人。”安重璋平靜道。
那一瞬間,我看到站在台階上的渾英眼里閃過一絲失落。
安重璋又道︰“我姓安,名重璋。你們要什麼,盡可向我來討。”商人們想是听過他的名號,立即扯住他討要說法。
我被擠到一邊,只能苦笑︰看來渾英破產屬實,只怕也沒有能力賄賂中使。那麼,剩下的便只有那個姓阿史那的商人了?
安重璋初步替渾英料理了欠下的賬,才喊上我離開。渾英在背後叫住他,頓了頓,才道︰“多謝。”安重璋嘆了口氣,只溫聲道︰“你多叫幾個族人來和你同住罷。再有這樣的事,你就來尋我。”
邊地的秋日沒有太多暖意,卻有足夠濃郁的色彩。遠處祁連山頂的雪色連著雲色,在陽光映照下,亮得極具侵略性,簡直有些刺目。安重璋望著那片白亮的雪和雲,閉了閉眼,低聲道︰“我和渾英有過婚約。”
我頷首,一個是鐵勒族人,一個是九姓胡人之後,這種外族婚姻很常見。
“阿英……她實則不喜漢人,也不敬重大唐皇帝。她說,渾部內附大唐,已有數代,可唐人仍然不肯像待漢人一樣待渾部的族人……河西各族混居,邊民有這般心思,也不足為奇。但……自從我曾祖涼國公起,我家一直忠于大唐皇帝。我很敬愛她,但又實在為難。”他說得委婉,但話中的無奈之意掩也掩不住。
渾英不能接受被區別對待,這其實是很多胡人都有的感受。而安重璋家是河西豪族,屬于本地長官也要著意禮敬的地方大豪。他的曾祖安興貴是凌煙閣功臣,到了他父親這輩,雖不如曾祖風采閃耀,也曾做過鄯州都督,所以他是真正的土豪,又是官二代,沒法代入渾英的情緒,也很自然。
政見不合導致的分手,一般是無法挽回的。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也或許他根本不需要安慰,于是我只能向路邊的餅販買了一個加糖的餅,塞給他。
我們約了過一日去尋阿史那盈科,便分開了。見時辰尚早,我便迫不及待地去尋王維。王維聞得我來訪,連忙迎了出來。我故意挑刺道︰“你並非倒屣相迎,可見心中不甚以我為意。”
他喊冤︰“你只管胡白!我寫字寫到一半,且放下了來迎你。”我一顧他身上,果見他袖口處微染墨漬,遂笑道︰“你寫的什麼字?”王維笑道︰“是一首詩。我正在苦思其中二字。”領我走入室中,指向案上鋪開的熟紙。我看時,只見那紙上寫的是︰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