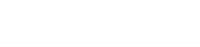“是报应!买卖人口、打老婆的报应!”
“肯定是那些冤死的女人来索命了!”
“那墙上、背上的叉……是阎王爷打的叉!判了罪的!”
各种诡异恐怖的传言在村民间交头接耳,越传越邪乎。以前那些买了媳妇、打过老婆的人家,如今个个提心吊胆,夜里不敢深睡,门窗多加两道栓也没用。丈夫看妻子的眼神里多了惊疑,婆婆对买来的媳妇也不敢再随意打骂,甚至有些人心里发毛,偷偷把锁人的链子、打人的棍棒扔到了山沟里。
一种无声的、却令人窒息的审判,笼罩了整个石涧村。作恶者终于开始品尝自己种下的恐惧,而一直笼罩在村子上空的愚昧与野蛮,第一次被一种更原始、更不可知的力量压制住。
王婆子还想撒泼打滚,去找族长评理,可族长家的大门紧闭,据说老爷子也吓病了。王二柱彻底蔫了,看到楚砚溪就像老鼠见了猫,晚上都不敢跟她睡一屋,自己抱着被子和王婆子挤一屋睡。
对于这一切,楚砚溪冷眼旁观。
她白天照常干活,沉默寡言,晚上则像暗夜骑士一般,用从山里采来的草药和一把剪刀、一捆绳索,用她的方式惩罚那些参与买卖人口的村民。
如果法律不能制裁这些作恶者,那好就用自己的方式来应对!
她要让恐惧扎根,让愚昧为罪恶付出代价。
就在全村被恐慌笼罩,人心惶惶之际,村口再次传来了动静。
这一次,阵仗更大。
陆哲回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他身后跟着十几号人——扛着摄像机的省电视台记者,面色凝重的乡政府书记和几位干部,还有全副武装的派出所民警,周警官和小张也在其中。一行人浩浩荡荡,再次踏上了石涧村的土地。
村民被召集到打谷场。
电视台的镜头扫过一张张惊恐未定的脸,扫过那些刚刚经历了“天谴”、眼神闪烁的村民。
乡政府的杨书记拿着喇叭,声音严肃:“乡亲们!我们接到举报,石涧村存在严重的拐卖妇女、虐待妇女的问题!这是违法犯罪行为!国家法律绝不容忍!”
周警官也站上前,犀利的目光扫视全场:“王老五的案子已经查清,春妮是清白的,但其他被拐卖妇女的权益必须得到保障!今天,我们就是来解决问题的。所有被卖到石涧村的妇女,只要愿意离开的,政府负责送你们回家!愿意留下的,必须保证不再有虐待行为,否则严惩不贷!”
村民们看着这阵势,听着喇叭里的法律宣传,再想想这几天诡异的“天谴”,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法律的压力和鬼神的恐惧双重作用下,没人再敢反抗。
王富国和族老们面面相觑,最终颤抖着表了态:“我们配合政府,配合调查……”
一家接一家,当初买来的媳妇被叫到面前,在镜头和干部的注视下,颤抖着说出自己的意愿。有的哭着想回家,有的犹豫地看着身边的男人和孩子,最终大部分都选择了离开这个噩梦之地。
“我要下山,我要回家!两个女儿,我也要带走。”春妮紧紧拉着两个女儿的手,第一个站到了民警身边,眼神坚定。
一个又一个女人勇敢地站在春妮身边,大声说出自己的选择。
楚砚溪站在人群边缘,看着眼前这一幕,眼眶有些湿润。
王二柱和王婆子缩在角落里,面如死灰,压根就不敢看她。他们这回终于明白了,这个曾经被他们认为老实可欺的新媳妇,并不是个好拿捏的主。
陆哲穿过人群,走到她面前,四目相对,千言万语都在其中。
透过她眼底的平静,陆哲看到了那份独属于她的、带着锋芒的坚韧。
他想起她那晚“十五”的手势,心潮起伏。陆哲知道,这是楚砚溪和自己约定再见面的日子。而这一回,自己并没有辜负她的托付与信任。
陆哲声音低沉,带着丝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怜惜:“结束了。”
楚砚溪微微颔首,阳光照在她脸上,镀上一层暖色。
她看着那些即将获得新生的女人,看着面前这个一次次试图帮助她、最终与她默契配合改变了局面的男人,心中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在这个陌生而残酷的世界里,有一个可以信任、可以并肩的“战友”,是多么重要。
“嗯,”她轻声应道,嘴角勾起一抹极淡却真实的弧度,“结束了。”
-----------------------
作者有话说:忘记设置更新时间了,到下午了才发现。赶紧补上今天的更新,明天9点照旧~
第26章 江城 27岁的楚同裕
石涧村的天, 彻底变了。
曾经对着楚砚溪耀武扬威的王婆子精气神都垮了,原本花白的头发被铰得参差不齐,新长出的发茬灰白交错, 使得她整个人看起来苍老了十岁不止。
王二柱更是废了。胯。下的伤虽不致命,但那种心理上的阉割感远比肉。体疼痛更摧残人。见到警察与记者, 他眼神躲闪,下意识地夹紧双腿,佝偻着背, 仿佛随时准备承受无形的鞭挞。
乡政府组织的解救工作队在村支书和派出所民警的陪同下,井然有序地开展工作。
这一次,连日来的“天谴”让村民们没有了之前的剑拔弩张,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的、胆战心惊的恐慌。
打谷场上,愿意离开的被拐妇女和她们的孩子站成了一排。
春妮紧紧拉着大丫和二丫的手, 脸上虽然还有沧桑, 但眼神里已经有了光。其他几个女人,有的神情怯懦,有的面带期盼,但都坚定地选择了离开这个噩梦之地。
工作队员逐一对她们进行登记,发放路费和临时安置证明。
楚砚溪站在队伍里,神色平静。她换上了一身半旧但干净的蓝布衫,头发利落地挽在脑后, 露出光洁的额头和冷静的眉眼。与周围那些或激动或惶恐的女人相比,她显得很冷静。
陆哲穿梭在人群中, 协助工作人员沟通,目光却时不时落在楚砚溪身上。看到她安然无恙,比上次见面时气色更好了些,他悬了多日的心才稍稍放下。
手续办理得出奇顺利。没有村民阻拦, 没有人撒泼打滚,王富国和几位族老远远站着,面色复杂,却终究没再上前。
登记手续办完,工作人员领着要离开的媳妇、孩子缓缓向村口移动。
下山的路,依旧崎岖难行。但因为有了期待与希望,每个人脸上都漾着轻松与欢乐。
楚砚溪和陆哲自然而然地走在了一起,落在了队伍稍后的位置。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陆哲侧过头,看着楚砚溪被山风吹拂的侧脸,轻声问道。他知道,以她的性格,绝不可能就此回归正常生活。
楚砚溪目视前方,脚步沉稳:“去江城。”
陆哲微微一怔:“江城?为什么是江城?”江城不是他的家乡,但他大学毕业后选择在那里工作,对江城也很熟悉。
楚砚溪沉默了片刻,像是在斟酌措辞。她的目光投向远处层峦叠嶂的山脉,眼神有些悠远:“我要去确认一些事情。”
停顿片刻之后,她的声音低了些:“我要确认,这里到底是我们之前那个世界的过去,还是另外一个……平行的世界。”
陆哲脚步一顿,愕然看向她。
楚砚溪没有过多的解释。
她现在要去确认,父亲是否收到了自己在上一次穿越传递的讯息。
上一次穿越是1985年,那个时候父亲20岁。现在1992年,父亲27岁,刚刚进入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记得上一次见到父亲时,他说他很喜欢派出所的工作,可为什么最终选择成为一名刑警?
楚砚溪眸光闪动,思绪已经飘到江城市公安局,那个她工作了七年的地方。
而陆哲,脑中瞬间闪过一个念头。
——过去?平行世界?
一个惊人的猜想在陆哲脑中形成,他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有些发干:“那个,你之前说,我们穿进的是一本叫《破茧》的纪实文学作品……”
“是。”楚砚溪肯定地回答。
陆哲的眼睛里闪动着莫名的光芒:“纪实文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经历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它不是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历史!是不是?”
“是。”楚砚溪再一次点头。
“真实发生过的历史?”陆哲嘴里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瞳孔骤然收缩,一个他从未敢深想的可能性浮上心头,“春妮、王老五、石涧村……甚至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真实存在过的?”
山风似乎在这一刻静止了。陆哲感觉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随即疯狂地擂动起来,血液冲上头顶,耳边嗡嗡作响。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那岂不是说……
“那我妈妈……”陆哲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也是真实存在的?她,她还活着?”
他急切地追问,眼中充满了希冀与恐惧交织的复杂情绪。童年时母亲所承受的家暴阴影,是他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但如果他真的是回到了过去,回到了1992年呢?他是不是能够保护好妈妈,不让她承受那样的痛苦?
楚砚溪看着瞬间失态的陆哲,轻声道:“上一次穿越,我回到江城,见到了我的父亲。他那个时候才20岁,风华正茂。”
她不需要说完,陆哲已经明白了。
1992年!现在是1992年!
他的父亲陆达坤,此时应该27岁,是江城某机械厂的青年工人,还是个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小混混”。而他的母亲沈静才22岁,从不幸的原生家庭逃离之后,留在江城一家小饭店打工,对未来怀着卑微的憧憬。
这个时候的父母,他们可能刚刚认识,甚至还没有开始交往。
巨大的、近乎荒谬的希望像潮水般淹没了陆哲。悲喜交加,让他一时语塞,眼眶不受控制地泛起湿意。
喜的是,母亲悲惨的命运还没有开始,还来得及改变。
悲的是,那个给他和母亲带来无尽痛苦的男人,此刻正年轻,可能正用虚伪的热情欺骗着年轻懵懂的母亲!
“陆达坤。”陆哲喃喃念出这个他痛恨又熟悉的的名字,手指关节因用力而泛白。
“沈静……”母亲温柔而哀伤的面容在他眼前清晰无比。
楚砚溪安静地看着陆哲,没有打扰此刻又悲又喜的他。
她理解陆哲此刻的震撼。
她自己何尝不是被“这个世界真实存在”这个念头灼烧着?她急于去江城,不正是为了探寻父亲的人生轨迹吗?
良久,陆哲才缓缓吐出一口气,平复着翻腾的心绪。
他看向楚砚溪的眼神里多了一丝复杂的情绪,那是一种奇异的共鸣感——他们不是偶然卷入事件的穿越者,而是可能改变历史的、背负着特殊使命的人。
“我跟你一起去江城。”陆哲的声音恢复了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石涧村的轮廓在身后逐渐模糊,最终隐匿于连绵的群山之中。
楚砚溪和陆哲下山之后,归心似箭地坐上了火车,来到久违的江城。
1992年的江城,与记忆中的现代都市截然不同。楼房不高,街道上自行车流如织,偶尔驶过的桑塔纳轿车显得格外气派,整个城市弥漫着一种蓬勃而又略显粗糙的活力。
这一切对楚砚溪和陆哲而言,既陌生又熟悉,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观看旧照片。
楚砚溪与陆哲分开行动。
楚砚溪来到老城区,找到了市刑侦支队一大队曾经所在地。那是一栋灰扑扑的、带着苏式建筑风格的三层小楼,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显得有些肃穆。
楚砚溪没有着急进去,而是在对街一个不太起眼的茶摊坐了下来。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公安局的门脸上,进出的人不多,偶尔有穿着橄榄绿警服或便装的身影匆匆而过。
楚砚溪的目光紧紧锁定着那扇大门,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粗糙的茶杯边缘,一言不发。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茶摊的老板已经开始准备收摊。
就在天色渐晚,几乎要以为今天等不到的时候,楚砚溪的身体突然微微绷直,她看到了!
一个年轻的身影走了出来。他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警服,没有戴帽子,身姿挺拔,步伐矫健,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疲惫与亢奋的神情,嘴角似乎还挂着一丝轻松笑意。
“肯定是那些冤死的女人来索命了!”
“那墙上、背上的叉……是阎王爷打的叉!判了罪的!”
各种诡异恐怖的传言在村民间交头接耳,越传越邪乎。以前那些买了媳妇、打过老婆的人家,如今个个提心吊胆,夜里不敢深睡,门窗多加两道栓也没用。丈夫看妻子的眼神里多了惊疑,婆婆对买来的媳妇也不敢再随意打骂,甚至有些人心里发毛,偷偷把锁人的链子、打人的棍棒扔到了山沟里。
一种无声的、却令人窒息的审判,笼罩了整个石涧村。作恶者终于开始品尝自己种下的恐惧,而一直笼罩在村子上空的愚昧与野蛮,第一次被一种更原始、更不可知的力量压制住。
王婆子还想撒泼打滚,去找族长评理,可族长家的大门紧闭,据说老爷子也吓病了。王二柱彻底蔫了,看到楚砚溪就像老鼠见了猫,晚上都不敢跟她睡一屋,自己抱着被子和王婆子挤一屋睡。
对于这一切,楚砚溪冷眼旁观。
她白天照常干活,沉默寡言,晚上则像暗夜骑士一般,用从山里采来的草药和一把剪刀、一捆绳索,用她的方式惩罚那些参与买卖人口的村民。
如果法律不能制裁这些作恶者,那好就用自己的方式来应对!
她要让恐惧扎根,让愚昧为罪恶付出代价。
就在全村被恐慌笼罩,人心惶惶之际,村口再次传来了动静。
这一次,阵仗更大。
陆哲回来了。
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他身后跟着十几号人——扛着摄像机的省电视台记者,面色凝重的乡政府书记和几位干部,还有全副武装的派出所民警,周警官和小张也在其中。一行人浩浩荡荡,再次踏上了石涧村的土地。
村民被召集到打谷场。
电视台的镜头扫过一张张惊恐未定的脸,扫过那些刚刚经历了“天谴”、眼神闪烁的村民。
乡政府的杨书记拿着喇叭,声音严肃:“乡亲们!我们接到举报,石涧村存在严重的拐卖妇女、虐待妇女的问题!这是违法犯罪行为!国家法律绝不容忍!”
周警官也站上前,犀利的目光扫视全场:“王老五的案子已经查清,春妮是清白的,但其他被拐卖妇女的权益必须得到保障!今天,我们就是来解决问题的。所有被卖到石涧村的妇女,只要愿意离开的,政府负责送你们回家!愿意留下的,必须保证不再有虐待行为,否则严惩不贷!”
村民们看着这阵势,听着喇叭里的法律宣传,再想想这几天诡异的“天谴”,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法律的压力和鬼神的恐惧双重作用下,没人再敢反抗。
王富国和族老们面面相觑,最终颤抖着表了态:“我们配合政府,配合调查……”
一家接一家,当初买来的媳妇被叫到面前,在镜头和干部的注视下,颤抖着说出自己的意愿。有的哭着想回家,有的犹豫地看着身边的男人和孩子,最终大部分都选择了离开这个噩梦之地。
“我要下山,我要回家!两个女儿,我也要带走。”春妮紧紧拉着两个女儿的手,第一个站到了民警身边,眼神坚定。
一个又一个女人勇敢地站在春妮身边,大声说出自己的选择。
楚砚溪站在人群边缘,看着眼前这一幕,眼眶有些湿润。
王二柱和王婆子缩在角落里,面如死灰,压根就不敢看她。他们这回终于明白了,这个曾经被他们认为老实可欺的新媳妇,并不是个好拿捏的主。
陆哲穿过人群,走到她面前,四目相对,千言万语都在其中。
透过她眼底的平静,陆哲看到了那份独属于她的、带着锋芒的坚韧。
他想起她那晚“十五”的手势,心潮起伏。陆哲知道,这是楚砚溪和自己约定再见面的日子。而这一回,自己并没有辜负她的托付与信任。
陆哲声音低沉,带着丝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怜惜:“结束了。”
楚砚溪微微颔首,阳光照在她脸上,镀上一层暖色。
她看着那些即将获得新生的女人,看着面前这个一次次试图帮助她、最终与她默契配合改变了局面的男人,心中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在这个陌生而残酷的世界里,有一个可以信任、可以并肩的“战友”,是多么重要。
“嗯,”她轻声应道,嘴角勾起一抹极淡却真实的弧度,“结束了。”
-----------------------
作者有话说:忘记设置更新时间了,到下午了才发现。赶紧补上今天的更新,明天9点照旧~
第26章 江城 27岁的楚同裕
石涧村的天, 彻底变了。
曾经对着楚砚溪耀武扬威的王婆子精气神都垮了,原本花白的头发被铰得参差不齐,新长出的发茬灰白交错, 使得她整个人看起来苍老了十岁不止。
王二柱更是废了。胯。下的伤虽不致命,但那种心理上的阉割感远比肉。体疼痛更摧残人。见到警察与记者, 他眼神躲闪,下意识地夹紧双腿,佝偻着背, 仿佛随时准备承受无形的鞭挞。
乡政府组织的解救工作队在村支书和派出所民警的陪同下,井然有序地开展工作。
这一次,连日来的“天谴”让村民们没有了之前的剑拔弩张,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的、胆战心惊的恐慌。
打谷场上,愿意离开的被拐妇女和她们的孩子站成了一排。
春妮紧紧拉着大丫和二丫的手, 脸上虽然还有沧桑, 但眼神里已经有了光。其他几个女人,有的神情怯懦,有的面带期盼,但都坚定地选择了离开这个噩梦之地。
工作队员逐一对她们进行登记,发放路费和临时安置证明。
楚砚溪站在队伍里,神色平静。她换上了一身半旧但干净的蓝布衫,头发利落地挽在脑后, 露出光洁的额头和冷静的眉眼。与周围那些或激动或惶恐的女人相比,她显得很冷静。
陆哲穿梭在人群中, 协助工作人员沟通,目光却时不时落在楚砚溪身上。看到她安然无恙,比上次见面时气色更好了些,他悬了多日的心才稍稍放下。
手续办理得出奇顺利。没有村民阻拦, 没有人撒泼打滚,王富国和几位族老远远站着,面色复杂,却终究没再上前。
登记手续办完,工作人员领着要离开的媳妇、孩子缓缓向村口移动。
下山的路,依旧崎岖难行。但因为有了期待与希望,每个人脸上都漾着轻松与欢乐。
楚砚溪和陆哲自然而然地走在了一起,落在了队伍稍后的位置。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陆哲侧过头,看着楚砚溪被山风吹拂的侧脸,轻声问道。他知道,以她的性格,绝不可能就此回归正常生活。
楚砚溪目视前方,脚步沉稳:“去江城。”
陆哲微微一怔:“江城?为什么是江城?”江城不是他的家乡,但他大学毕业后选择在那里工作,对江城也很熟悉。
楚砚溪沉默了片刻,像是在斟酌措辞。她的目光投向远处层峦叠嶂的山脉,眼神有些悠远:“我要去确认一些事情。”
停顿片刻之后,她的声音低了些:“我要确认,这里到底是我们之前那个世界的过去,还是另外一个……平行的世界。”
陆哲脚步一顿,愕然看向她。
楚砚溪没有过多的解释。
她现在要去确认,父亲是否收到了自己在上一次穿越传递的讯息。
上一次穿越是1985年,那个时候父亲20岁。现在1992年,父亲27岁,刚刚进入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记得上一次见到父亲时,他说他很喜欢派出所的工作,可为什么最终选择成为一名刑警?
楚砚溪眸光闪动,思绪已经飘到江城市公安局,那个她工作了七年的地方。
而陆哲,脑中瞬间闪过一个念头。
——过去?平行世界?
一个惊人的猜想在陆哲脑中形成,他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有些发干:“那个,你之前说,我们穿进的是一本叫《破茧》的纪实文学作品……”
“是。”楚砚溪肯定地回答。
陆哲的眼睛里闪动着莫名的光芒:“纪实文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经历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它不是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历史!是不是?”
“是。”楚砚溪再一次点头。
“真实发生过的历史?”陆哲嘴里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瞳孔骤然收缩,一个他从未敢深想的可能性浮上心头,“春妮、王老五、石涧村……甚至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真实存在过的?”
山风似乎在这一刻静止了。陆哲感觉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随即疯狂地擂动起来,血液冲上头顶,耳边嗡嗡作响。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那岂不是说……
“那我妈妈……”陆哲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也是真实存在的?她,她还活着?”
他急切地追问,眼中充满了希冀与恐惧交织的复杂情绪。童年时母亲所承受的家暴阴影,是他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但如果他真的是回到了过去,回到了1992年呢?他是不是能够保护好妈妈,不让她承受那样的痛苦?
楚砚溪看着瞬间失态的陆哲,轻声道:“上一次穿越,我回到江城,见到了我的父亲。他那个时候才20岁,风华正茂。”
她不需要说完,陆哲已经明白了。
1992年!现在是1992年!
他的父亲陆达坤,此时应该27岁,是江城某机械厂的青年工人,还是个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小混混”。而他的母亲沈静才22岁,从不幸的原生家庭逃离之后,留在江城一家小饭店打工,对未来怀着卑微的憧憬。
这个时候的父母,他们可能刚刚认识,甚至还没有开始交往。
巨大的、近乎荒谬的希望像潮水般淹没了陆哲。悲喜交加,让他一时语塞,眼眶不受控制地泛起湿意。
喜的是,母亲悲惨的命运还没有开始,还来得及改变。
悲的是,那个给他和母亲带来无尽痛苦的男人,此刻正年轻,可能正用虚伪的热情欺骗着年轻懵懂的母亲!
“陆达坤。”陆哲喃喃念出这个他痛恨又熟悉的的名字,手指关节因用力而泛白。
“沈静……”母亲温柔而哀伤的面容在他眼前清晰无比。
楚砚溪安静地看着陆哲,没有打扰此刻又悲又喜的他。
她理解陆哲此刻的震撼。
她自己何尝不是被“这个世界真实存在”这个念头灼烧着?她急于去江城,不正是为了探寻父亲的人生轨迹吗?
良久,陆哲才缓缓吐出一口气,平复着翻腾的心绪。
他看向楚砚溪的眼神里多了一丝复杂的情绪,那是一种奇异的共鸣感——他们不是偶然卷入事件的穿越者,而是可能改变历史的、背负着特殊使命的人。
“我跟你一起去江城。”陆哲的声音恢复了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石涧村的轮廓在身后逐渐模糊,最终隐匿于连绵的群山之中。
楚砚溪和陆哲下山之后,归心似箭地坐上了火车,来到久违的江城。
1992年的江城,与记忆中的现代都市截然不同。楼房不高,街道上自行车流如织,偶尔驶过的桑塔纳轿车显得格外气派,整个城市弥漫着一种蓬勃而又略显粗糙的活力。
这一切对楚砚溪和陆哲而言,既陌生又熟悉,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观看旧照片。
楚砚溪与陆哲分开行动。
楚砚溪来到老城区,找到了市刑侦支队一大队曾经所在地。那是一栋灰扑扑的、带着苏式建筑风格的三层小楼,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显得有些肃穆。
楚砚溪没有着急进去,而是在对街一个不太起眼的茶摊坐了下来。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公安局的门脸上,进出的人不多,偶尔有穿着橄榄绿警服或便装的身影匆匆而过。
楚砚溪的目光紧紧锁定着那扇大门,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粗糙的茶杯边缘,一言不发。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茶摊的老板已经开始准备收摊。
就在天色渐晚,几乎要以为今天等不到的时候,楚砚溪的身体突然微微绷直,她看到了!
一个年轻的身影走了出来。他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警服,没有戴帽子,身姿挺拔,步伐矫健,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疲惫与亢奋的神情,嘴角似乎还挂着一丝轻松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