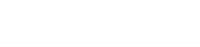青年桌上铺着一张画卷,正执笔作画。
姜宁穗:“裴公子,你受了伤,又失血过多,不宜再劳累,还是早些歇息的好。”
裴铎掀眸,隔着窗牖看向院中的姜宁穗。
女人纤细身姿在清泠泠的月色下愈显薄弱。
这几日她总避着他,即使在饭桌上也低着头。
现下好了。
嫂子终于不再躲着他了。
青年颔首:“知晓了。”
他垂下眸,蘸了墨汁的笔尖在画卷上描摹。
渐渐地,画卷上的美人图初见雏形。
女人穿着小衣,小衣细带绕过后颈,盈盈一握的细腰挂着摇摇欲坠的细带,那飘摇的尾端坠在女人的尾椎骨上。
一双水盈盈的杏眸窝了一汪水。
可怜且无措的望着他。
青年指尖点在画中女人的水眸上,细细抚摸,沿着女人柔软的脸部线条滑向颈部,那有如实质的触摸,渐渐抚上女人裸露的肩膀,雪峰,纤腰——
最后落在那朵绽开的花瓣上。
青年听见隔壁传来女人细软的声音,是独属于对她郎君的温柔。
她唤那个废物郎
君。
她被那个废物抱住了。
她郎君在亲她。
青年捻在花瓣处的指尖倏地用了力道,只见一团墨渍晕开在花瓣上。
似莹莹白灼,靡艳撩人。
隔壁屋里。
姜宁穗推了推赵知学肩膀,偏过头躲开他不断寻来的吻。
经过上次一事,姜宁穗对这种事几乎有了阴影。
尤其耳力极好的裴公子就在隔壁。
她缩在赵知学怀里,柔声道:“郎君,我们改日罢。”
改日裴公子不在,门窗都闭好再行此事,不然她不放心。
赵知学想起那日姜宁穗忽然从他身上下来躲进被窝里哭的上气不接下气,也不敢强求她,只望着漆黑的屋顶无声叹气。
娶的妻子能看不能碰。
这日子何时是个头。
夜深了,大开的窗牖里依旧亮着一盏灯。
寒风肆虐侵袭,吹的那盏灯明灭不定。
裴铎卷起梨花桌案上的那幅画,将画卷放进桌案旁的画笥中。
画笥里已收纳了五幅画。
每一幅都是嫂子。
嫂子日日进他屋里,却从未碰过他屋里其它东西。
但凡她打开一幅画看一眼,只需一眼,便会知晓他的心思。
明日元宵节,学堂休沐一日。
姜宁穗翌日一早起来才从郎君口中得知,他今日与几位同窗约好游湖,问她去不去。
姜宁穗摇头:“郎君去罢,我就不去了。”
游湖的都是学堂里的学子,她跟着去不合适。
赵知学起身从后面抱住姜宁穗,下颔搁在她肩上,歪头在她侧脸亲了下:“今日元宵节,我听同窗说隆昌县今夜有灯会,等游湖回来,我今晚带你去灯会转转。”
姜宁穗从未见过灯会是什么样。
她转身望着赵知学,秀丽柔和的眉眼里映着亮色:“郎君,灯会好看吗?”
赵知学笑道:“好不好看,今晚带你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姜宁穗眉眼弯起,第一次期待夜晚来临。
吃早饭时,赵知学问裴铎去不去游湖。
青年淡声道:“不去。”
这个答案在赵知学意料之中。
学堂里,同窗们偶尔结伴做什么,裴弟向来不会参与。
他今日一问,不过也是与裴弟客套一番。
吃过早饭赵知学就走了。
姜宁穗将灶房收拾干净,出来看到裴公子屋门开着。
她走过去,站在屋外轻声问道:“裴公子,你现在去医馆换药吗?”
青年合上书籍:“嗯。”
他起身出门:“嫂子同我一起去吗?”
姜宁穗:“嗯,我给大夫说一声,再给你抓点补气血的汤药。”
她看了眼裴公子的左手,白色细布上洇着红色血迹。
方才吃早饭,裴公子左手并未搭在桌上,她没注意到。
现下一看,竟又流了这么多血。
姜宁穗不敢耽搁,回屋再次将文钱塞进袖子里,与裴公子一道出门。
这次去换药买药,姜宁穗先一步将钱塞到大夫手里。
一共二十八文钱。
青年看着女人毫不心疼的模样,冷峻的眉峰虚虚一抬。
两人走出医馆,裴铎道:“今日让嫂子破费了。”
姜宁穗:“不算破费,若是没有裴公子与那位主家牵桥搭线,我也挣不到这些钱,比起裴公子对我的恩情,这些文钱不算什么。”
青年撩起眼皮,瞥了眼走在身旁的女人。
她对他好。
也只是因为那些恩。
可这哪够。
他想要的可不止这些。
若嫂子知晓他想杀了她郎君,想要她,想将她囚于他身边。
她还会想着还他这些恩情吗?
“嫂子喜欢灯会?”
青年突兀一问。
姜宁穗怔了一下,杏眸里漾出从未有过的新奇亮色:“我没看过灯会,不知道灯会是什么样。”
姜宁穗期待着郎君回来带她去县城看灯会。
她今天一整日心情都不错。
晌午穆花来家里找姜宁穗,也看出她心情甚好,便笑着问:“姜娘子这是碰着什么喜事了,从我进门就见你脸上带着笑,跟捡了钱似的。”
姜宁穗没想到自己表现的这般明显。
她道:“我郎君说晚上带我去县城看灯会。”
穆嫂子笑起来:“难怪姜娘子这么高兴,赵郎君有心了。”
穆嫂子坐了半个时辰就走了。
姜宁穗一下午都待在家里,看着给裴公子熬好汤药端给他。
暮色四合,屋里亮起灯盏。
姜宁穗等了整整一日,可直到天黑郎君都没回来。
姜宁穗期待了一整日的心沉沉落底,杏眸里的亮色也黯淡下来。
或许郎君有事耽搁了罢。
亦或是,郎君与同窗去了灯会,都是男子,她一个妇人跟着不合适。
姜宁穗平息好内心的失落,起身正要开门去去灶房,屋门突然被叩响。
她以为郎君回来了,满怀欣喜的打开房门。
不曾想,门外的人是裴公子。
裴铎将女人眸底的失望尽收眼底,乌黑的瞳仁里渗出清寒冷意。
见来人不是她郎君。
就这么失望?
可惜。
自从嫂子来镇上这小半年,她一次又一次,等来的人都是他。
她心里的好郎君食言了。
姜宁穗:“裴公子,你受了伤,又失血过多,不宜再劳累,还是早些歇息的好。”
裴铎掀眸,隔着窗牖看向院中的姜宁穗。
女人纤细身姿在清泠泠的月色下愈显薄弱。
这几日她总避着他,即使在饭桌上也低着头。
现下好了。
嫂子终于不再躲着他了。
青年颔首:“知晓了。”
他垂下眸,蘸了墨汁的笔尖在画卷上描摹。
渐渐地,画卷上的美人图初见雏形。
女人穿着小衣,小衣细带绕过后颈,盈盈一握的细腰挂着摇摇欲坠的细带,那飘摇的尾端坠在女人的尾椎骨上。
一双水盈盈的杏眸窝了一汪水。
可怜且无措的望着他。
青年指尖点在画中女人的水眸上,细细抚摸,沿着女人柔软的脸部线条滑向颈部,那有如实质的触摸,渐渐抚上女人裸露的肩膀,雪峰,纤腰——
最后落在那朵绽开的花瓣上。
青年听见隔壁传来女人细软的声音,是独属于对她郎君的温柔。
她唤那个废物郎
君。
她被那个废物抱住了。
她郎君在亲她。
青年捻在花瓣处的指尖倏地用了力道,只见一团墨渍晕开在花瓣上。
似莹莹白灼,靡艳撩人。
隔壁屋里。
姜宁穗推了推赵知学肩膀,偏过头躲开他不断寻来的吻。
经过上次一事,姜宁穗对这种事几乎有了阴影。
尤其耳力极好的裴公子就在隔壁。
她缩在赵知学怀里,柔声道:“郎君,我们改日罢。”
改日裴公子不在,门窗都闭好再行此事,不然她不放心。
赵知学想起那日姜宁穗忽然从他身上下来躲进被窝里哭的上气不接下气,也不敢强求她,只望着漆黑的屋顶无声叹气。
娶的妻子能看不能碰。
这日子何时是个头。
夜深了,大开的窗牖里依旧亮着一盏灯。
寒风肆虐侵袭,吹的那盏灯明灭不定。
裴铎卷起梨花桌案上的那幅画,将画卷放进桌案旁的画笥中。
画笥里已收纳了五幅画。
每一幅都是嫂子。
嫂子日日进他屋里,却从未碰过他屋里其它东西。
但凡她打开一幅画看一眼,只需一眼,便会知晓他的心思。
明日元宵节,学堂休沐一日。
姜宁穗翌日一早起来才从郎君口中得知,他今日与几位同窗约好游湖,问她去不去。
姜宁穗摇头:“郎君去罢,我就不去了。”
游湖的都是学堂里的学子,她跟着去不合适。
赵知学起身从后面抱住姜宁穗,下颔搁在她肩上,歪头在她侧脸亲了下:“今日元宵节,我听同窗说隆昌县今夜有灯会,等游湖回来,我今晚带你去灯会转转。”
姜宁穗从未见过灯会是什么样。
她转身望着赵知学,秀丽柔和的眉眼里映着亮色:“郎君,灯会好看吗?”
赵知学笑道:“好不好看,今晚带你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姜宁穗眉眼弯起,第一次期待夜晚来临。
吃早饭时,赵知学问裴铎去不去游湖。
青年淡声道:“不去。”
这个答案在赵知学意料之中。
学堂里,同窗们偶尔结伴做什么,裴弟向来不会参与。
他今日一问,不过也是与裴弟客套一番。
吃过早饭赵知学就走了。
姜宁穗将灶房收拾干净,出来看到裴公子屋门开着。
她走过去,站在屋外轻声问道:“裴公子,你现在去医馆换药吗?”
青年合上书籍:“嗯。”
他起身出门:“嫂子同我一起去吗?”
姜宁穗:“嗯,我给大夫说一声,再给你抓点补气血的汤药。”
她看了眼裴公子的左手,白色细布上洇着红色血迹。
方才吃早饭,裴公子左手并未搭在桌上,她没注意到。
现下一看,竟又流了这么多血。
姜宁穗不敢耽搁,回屋再次将文钱塞进袖子里,与裴公子一道出门。
这次去换药买药,姜宁穗先一步将钱塞到大夫手里。
一共二十八文钱。
青年看着女人毫不心疼的模样,冷峻的眉峰虚虚一抬。
两人走出医馆,裴铎道:“今日让嫂子破费了。”
姜宁穗:“不算破费,若是没有裴公子与那位主家牵桥搭线,我也挣不到这些钱,比起裴公子对我的恩情,这些文钱不算什么。”
青年撩起眼皮,瞥了眼走在身旁的女人。
她对他好。
也只是因为那些恩。
可这哪够。
他想要的可不止这些。
若嫂子知晓他想杀了她郎君,想要她,想将她囚于他身边。
她还会想着还他这些恩情吗?
“嫂子喜欢灯会?”
青年突兀一问。
姜宁穗怔了一下,杏眸里漾出从未有过的新奇亮色:“我没看过灯会,不知道灯会是什么样。”
姜宁穗期待着郎君回来带她去县城看灯会。
她今天一整日心情都不错。
晌午穆花来家里找姜宁穗,也看出她心情甚好,便笑着问:“姜娘子这是碰着什么喜事了,从我进门就见你脸上带着笑,跟捡了钱似的。”
姜宁穗没想到自己表现的这般明显。
她道:“我郎君说晚上带我去县城看灯会。”
穆嫂子笑起来:“难怪姜娘子这么高兴,赵郎君有心了。”
穆嫂子坐了半个时辰就走了。
姜宁穗一下午都待在家里,看着给裴公子熬好汤药端给他。
暮色四合,屋里亮起灯盏。
姜宁穗等了整整一日,可直到天黑郎君都没回来。
姜宁穗期待了一整日的心沉沉落底,杏眸里的亮色也黯淡下来。
或许郎君有事耽搁了罢。
亦或是,郎君与同窗去了灯会,都是男子,她一个妇人跟着不合适。
姜宁穗平息好内心的失落,起身正要开门去去灶房,屋门突然被叩响。
她以为郎君回来了,满怀欣喜的打开房门。
不曾想,门外的人是裴公子。
裴铎将女人眸底的失望尽收眼底,乌黑的瞳仁里渗出清寒冷意。
见来人不是她郎君。
就这么失望?
可惜。
自从嫂子来镇上这小半年,她一次又一次,等来的人都是他。
她心里的好郎君食言了。